|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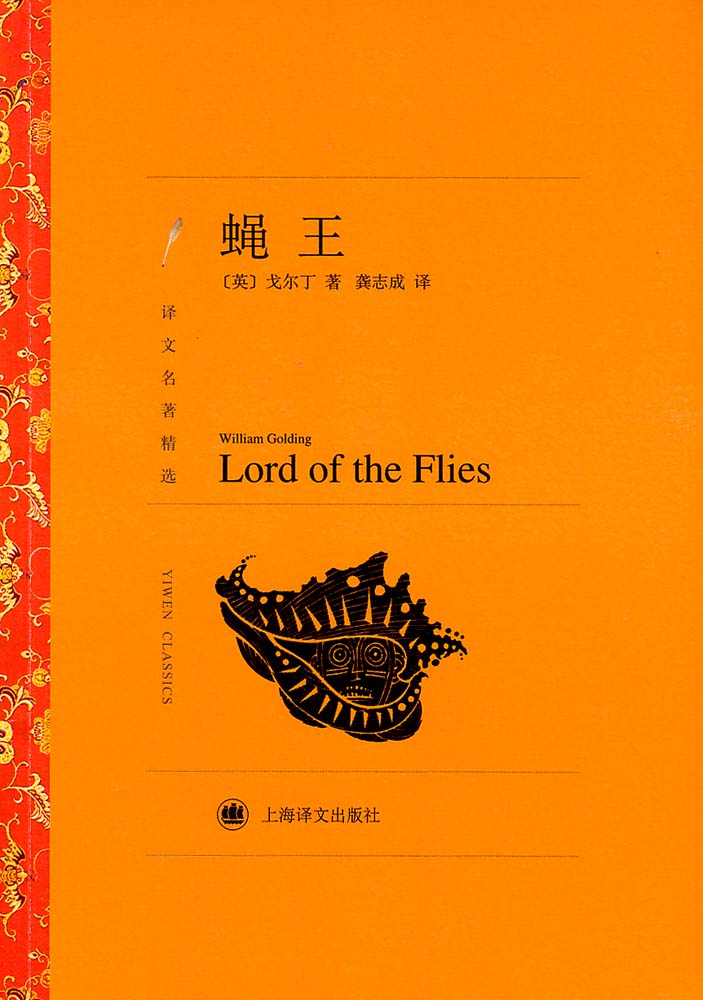 2011年,美国黑人女作家杰丝米妮·瓦德凭借描写卡特里娜飓风的小说《拾骨》获得该年度的美国国家图书奖(小说类)。在颁奖现场,瓦德发表了获奖感言:“我知道我要写的是穷人、黑人、南方乡下人的故事……从那些被我们忽视的边缘文化中,可以看到我们的故事具有普遍意义,我们的生活和他们一样忧虑、有趣和重要。这是一部关于我生命的作品。这只是开始。” 2011年,美国黑人女作家杰丝米妮·瓦德凭借描写卡特里娜飓风的小说《拾骨》获得该年度的美国国家图书奖(小说类)。在颁奖现场,瓦德发表了获奖感言:“我知道我要写的是穷人、黑人、南方乡下人的故事……从那些被我们忽视的边缘文化中,可以看到我们的故事具有普遍意义,我们的生活和他们一样忧虑、有趣和重要。这是一部关于我生命的作品。这只是开始。”
面对满堂的记者、评委和嘉宾,你不可能从“穷人”、“黑人”“南方乡下人”、“忽视的边缘文化”这类大词中突围而出,而这正是新闻与文学的区别所在。关于2005年席卷并重创美国南方大部地区的卡特里娜飓风,我们从公共媒体、舆论中看到的是因救灾不力而暴露的体制漏洞,以及大灾大难下各种人性恶的膨胀,中国国内甚至有部分媒体以此衡量中美两国体制和民情的优劣。但这只是从新闻层面来解读这起重大灾难,而好的文学则必须超脱这个层面而发掘更深层次的东西。
《拾骨》迥异于公共层面就这个话题所做的探讨。在这部小说中,“黑人”这个字眼只出现过一次,“白人”出现过三次,至于“穷人”、“乡下人”、“忽视的边缘文化”等则一次也没有出现。杰丝米妮·瓦德显然对这些足够表现政治觉悟的大词兴味索然,她的兴趣可以说是微观性的,也就是以人类学家田野考察的耐心和细致,像纪录片镜头那样去关注一家一室的生活、福祉和痛苦。经由这样的手法,这囿于一隅的邮票般大小的方寸之地,渐渐浮现出沉潜于表象之下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并非单纯到可以用体制优劣、经济贫富,或者人性善恶来定义,它们蕴含着丰富的人文底蕴,牢牢接榫着它们建筑其上的这块土地的“地气”。
小说描写了“荒木镇”大洼地黑人社区某个家庭在卡特里娜飓风袭击前后十二天的生活。这户人家的母亲已经去世,父亲克劳德是个酒鬼,叙述主人公“我”,十四岁的伊丝不幸怀上了身孕,十六岁的哥哥斯奇塔驯狗,十七岁的哥哥兰德尔打球,还有一个七岁的弟弟朱尼尔成天淘气。整本书的故事就在这家人噼噼啪啪地修房子、鬼鬼祟祟地呕吐和尿急、驯狗、打球和吵闹中,迎来灾难性的飓风。表面上,这个小说读来就像青春期成长故事一样平淡,也像各种游戏和打闹终究只是小孩子的玩意儿,但其实不是。“地气”才是这本小说真正的主角,它在小说的前十章中,化身为斯奇塔辛苦训练的斗犬琪娜,最后两章则化身为卡特里娜飓风。小说一多半的篇幅是围绕斯奇塔养狗、驯狗、斗狗、搭狗窝、给狗洗澡、除菌灭虱、打预防针展开的,为打预防针斯奇塔还领着兄弟姐妹和一干朋友犯险偷盗白人的农庄。
为什么琪娜在这本书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从经济层面上来看,训练琪娜成为战无不胜的斗犬,可以为斯奇塔支付今后的学费、为兰德尔打进职业篮球队铺路,眼下则可以改善因父亲半失业而造成的家庭窘境。但这还远远不是全部。小说写到斯奇塔不顾兰德尔劝说,坚持琪娜在产后立刻进行斗犬比赛,即使重伤后将危及狗崽的生命也在所不惜。为什么?
如果以一种局外的、成人的、高高在上的、新闻专业的眼光,来看待树林中由十几个男孩组织的斗狗比赛,我们的印象大概就会停留在城市街头青少年那种聚众斗殴的场面,我们会觉得,这些孩子真是既幼稚又无聊。但《拾骨》中的这些男孩子却异常严肃认真,并且,作者杰丝米妮·瓦德的描写也是异常严肃认真,没有调侃,没有嘲弄,没有谐谑。可以说,作者以一种自然主义的笔法、巨细靡遗地写出了斗狗比赛的实况:呐喊、撕咬、尘土、鲜血,其残酷堪比书末卡特琳娜飓风掀起的狂风巨浪。也就是说,作者和她笔下的男孩子们,都将斗狗视作事关生死的大事,因为斗狗的结果将重新调整本地黑人青少年复杂的力量平衡,就如森林部落的印第安人通过某些仪式划定势力范围,牵涉的不仅是生死,还有尊严、荣辱、生计的来源以及日后的命途。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到一个事实,即人与其所寓居的土地之间,存在一种相互影响、相互牵制的关系。斯奇塔在嘴里练刀片也好,“我”想方设法打掉腹中的胎儿也好,或者父亲时不时把自己灌得半死也罢,与其说出自一种幼稚的孩子气,或者甜腻腻的“美国梦”的失落,毋宁说是这片土地自然生成的结果。它塑造了人的骨头、血肉、性格和心灵,它的起始源远流长,不是单一的、某个历史阶段中的种族和经济问题所能解答,这也是《拾骨》从来不探讨这些问题的原因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