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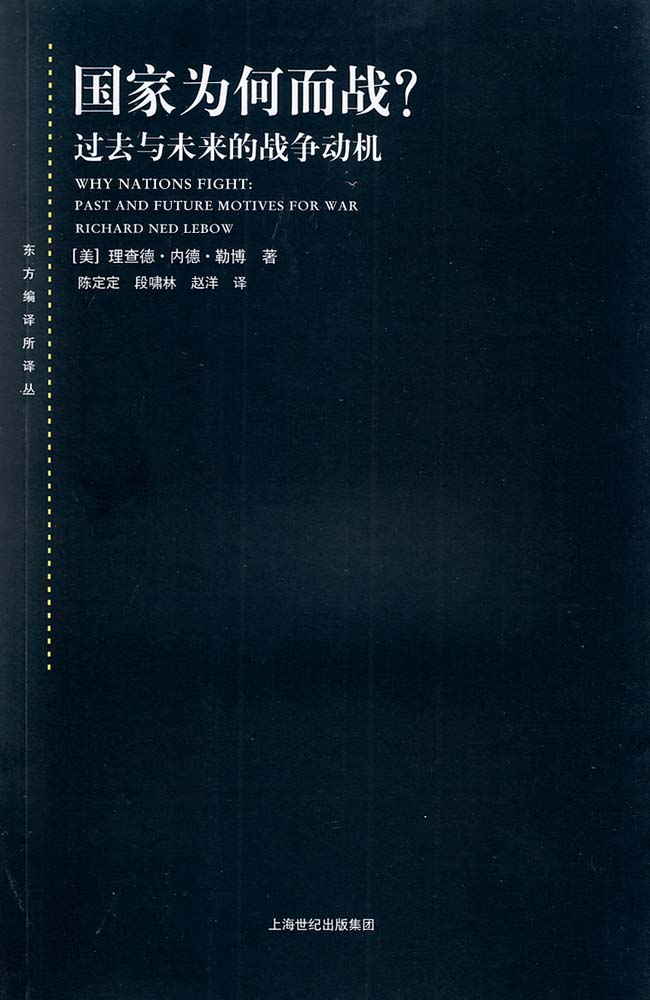 战争可以说是最为恒久的一项人类活动,从原始部落时代起它就与人类的历史如影随形。无论是讴歌、称颂还是痛斥、否定战争,人们总在花费大量的笔墨描述战争。战争不仅是文学作品最永恒的主题之一,还催生了无数的军事著作——政治家和将军们苦心研究兵法,希望对历史战例的了解能帮助他们在未来的战役中获胜。在人类不断改进杀人工具和技巧的过程中,战争也变得日益残酷和恐怖,而核时代的到来更是永久性地改变了人类的战争意识。 战争可以说是最为恒久的一项人类活动,从原始部落时代起它就与人类的历史如影随形。无论是讴歌、称颂还是痛斥、否定战争,人们总在花费大量的笔墨描述战争。战争不仅是文学作品最永恒的主题之一,还催生了无数的军事著作——政治家和将军们苦心研究兵法,希望对历史战例的了解能帮助他们在未来的战役中获胜。在人类不断改进杀人工具和技巧的过程中,战争也变得日益残酷和恐怖,而核时代的到来更是永久性地改变了人类的战争意识。
然而,也许正是战争司空见惯,让人习以为常,学者才不怎么努力追溯它们的起源,或者只是用“人的原始本能”等宏大概念一笔带过。从《孙子兵法》到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学者们更喜欢研究战争过程,指导将军们如何赢得战争,而不是战争为何会发生。在学术史上,对战争起因与动机的综合性研究很晚才出现,成为一个新领域,而美国学者理查德·内德·勒博所著的《国家为何而战?——过去与未来的战争动机》,在严谨性、系统性等方面,也许是这一领域不可多见的杰作。
研究战争的动机有其现实意义。刚刚过去的20世纪是很难定义的一百年,它见证了和平主义在全球的风起云涌,也见证了历史上最恐怖的战争。在现代,国家间战争发生的频率的确在降低,但造成的死伤人数超出以往,如果再加上国内冲突、种族屠杀、政治清洗等因素,人们在现代死于政治暴力的几率也许并不比过去低。因为战争的破坏性增大了,所以想办法避免战争的爆发也变得更为迫切,而更好地了解导致战争的原因,有助于人们更好地降低战争发生的几率。
勒博选择用一种系统化、模型化的方式研究战争。他将战争的参与国分为主导大国、大国、衰落大国、崛起国家和弱国,动机则分为五类:安全、物质利益、地位、报复和其他动机。战争的动机并不等于战争的目标,比如,夺取别国领土是常见的战争目标,但背后的动机却可能多种多样,如获取资源(即物质利益)、增进安全或者复仇等,而他只用动机作为区分不同战争的依据。
现实主义者对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有他们的解释:从修昔底德描述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直到今天,情况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尽管现代社会的公共舆论可能变得更加反战了,但政治家还是有足够的煽惑技巧来把民众聚集到“保家卫国”的大旗之下。现实主义者的论断所依据的根本基础是,人类的本性没有发生变化,而当前的国际体系仍然处于高度的无政府状态,没有一个更高的权威来约束民族国家的行为,因此当前各国开战的可能性也许与斯巴达、雅典一样高。
作为这种观点的批判者,勒博对战争在当代爆发几率的降低,抱着一种“乐观的审慎态度”。毕竟,在2500多年前,雅典与斯巴达、罗马与迦太基,分别作为当时世界对立的两极,都头也不回地投入到了争霸战争之中,而上个世纪的“冷战”最终却有一个和平的收场,这无疑是个更令人乐观的征兆。
当然,更深层次的基础是勒博对国际关系性质的认识。根据现实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的研究范式,外交政策总是执政者从战略角度进行理性思考的结果,其目标是提升本国相对于别国的力量,而就像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战争往往是外交这一政治政策的延续,因而也是理性的利益计算的产物。但是勒博争辩道,利益并不是影响国际关系的唯一因素,荣誉意识、仇恨、报复心,甚至毫无来由的敌意,通常也是重要的变量,而在很多时候国家都会为了与安全、利益完全无关的原因而开兵见仗,如果这些变量变弱了,战争的冲动就会降低。
在本书之前作者还写了《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一书,那是理解本书的基础。在该书中,作者将他的理论构建在一个简化的人类动机模型之上。以可上溯至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为依据,作者认为理性、情绪和欲望是人类最根本的三种驱动力,而如果理性不能约束情绪和欲望,如果某国对欲望的追求降低了他国满足欲望的可能性,就会产生第四种驱动力——恐惧。在他看来,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以欲望为基础,现实主义以恐惧为基础,但情绪这个因素却往往被现代的社会科学与哲学所忽视。而事实上情绪因素无处不在,比如,从古希腊城邦至今,他人的尊重是人类永恒的追求,虽然国家作为一种制度本身没有情绪,但它承载了人的心理需求——既包括国家的管理者,也包括对国家产生心理认同的普通国民。而大部分的战争都与领导人或国民的情绪密切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