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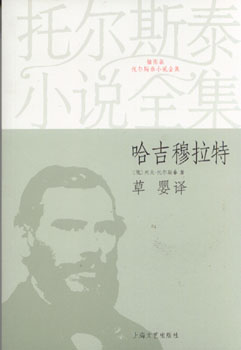 人人都说读书是一件彻底私人的事情,但有时候我喜欢一边读书一边玩一个无聊的想象游戏:如果不知道这本书作者是谁,我是否还能读完它,或者说是否还能发出现今这种赞叹? 人人都说读书是一件彻底私人的事情,但有时候我喜欢一边读书一边玩一个无聊的想象游戏:如果不知道这本书作者是谁,我是否还能读完它,或者说是否还能发出现今这种赞叹?
我们对一本书的评价,到底会受到多少其既有地位的影响,我们的阅读经历,在多大程度上会漂浮在他人的眼光之上?
有些书不需要深思熟虑:《红楼梦》的作者就算在市场上卖猪,我也要飞奔过去紧握他油腻腻的双手说:“你实在写得太好了!给我两斤五花肉吧,再来半斤猪肝!”
我不会喜欢任何一本巴尔扎克,我会喜欢任何一本契诃夫。《悲惨世界》前面关于巴黎市政建设的冗长描写会让我非常不耐烦,当然最后我还是会被冉阿让和沙威的选择感动。我必然会一口气读完《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依然会让我深深着迷,宗教大法官那一章依然会是我对“自由”这个词语理解的来源。
我会埋怨《群魔》结构一塌糊涂,情节啰里啰嗦,主角居然书写了一小半才正式出场,但里面的一些句子,即使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名字的照耀,依然灼灼闪光,比如基里洛夫说:“不,我不相信未来的永恒生活,而是相信这儿的永恒生活。存在着一些瞬间,您可以达到这些瞬间,而时间却会突然停止,那时它就会成为永恒。”
如果熬过前面几章冗长的人名和法语对话,我能够进入《战争与和平》的世界,但我会很不高兴托尔斯泰安排娜塔莎发胖的情节,以及最后那三万字评论文字完全是垃圾。阿城也说他读《战争与和平》都不忍心读后面三万字,因为不忍心看一流的小说家变成不入流的思想家。《安娜·卡列尼娜》放在任何时代置于任何人的名下都是堪称伟大的作品,帕慕克在《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里提了几十次这本书,而且几乎每次都是安娜在火车上读书那个场景。
和前面这些笃定的答案不同,最近托尔斯泰给我提出了一个让人摇摆游移的问题:我喜欢他的《哈吉穆拉特》吗?
这部小说一直没有出过中文单行本,深深隐藏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那套《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四卷里,我能找到它的原因是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里说这是他读过最好的短篇小说。《西方正典》是文学批评界的圣经,所以我先读了这篇《托尔斯泰和英雄主义》,再读了一百页出头的《哈吉穆拉特》,但我还是拿不准这件事:我喜欢它吗?
这篇不到十万字的小说,托尔斯泰从1896年写到1904年,1898年至1901年这三年他中断了这篇小说的写作,查阅大量历史资料,像记者一样询问诸多历史当事人。八年中他几易其稿,而且始终不允许家人发表,1910年托尔斯泰去世,1912年《哈吉穆拉特》作为遗稿面世。
因为涉及高加索战争,被俄国书报检查机关大量删改,一直到1918年,我们现在读到的版本才得以出版。小说的故事和结构都非常简单,也大致和历史相符:鞑靼人哈吉穆拉特本是高加索穆斯林教派领袖沙米尔的副手,因为战功赫赫,沙米尔疑心渐增,扣押其家人为人质。1851年底哈吉穆拉特投诚沙皇,冀望俄国以俘虏交换其家人,并允诺到时会帮助俄国击败沙米尔,但他渐渐发现俄国人不过让其在等待中虚耗时光。1852年4月他痛下决心逃跑,最终被俄国追兵砍下头颅。
托尔斯泰在故事开始前写了一段引言,描写顽强的牛蒡花,“人战胜了一切,毁灭了成百万的草芥,而这一棵却依然不屈服”。牛蒡花又名“鞑靼花”,这样赤裸裸的比喻抒情,简直让人想到我们的《荔枝蜜》,不敢相信这是书写历史和人性的大师托尔斯泰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反复修改的作品。
以赛亚·伯林在《俄国思想家》中说晚年托尔斯泰念念执著的主题:“我们一切困惑的解决之道近在眉睫——答案就在我们身畔周遭,俯拾皆是,昭昭然如化日天光,只要我们不自闭眼睛,不四处瞻望,而肯凝神注目,就会看到清明、单纯、不可抗拒的真理正在瞪着我们。”这部《哈吉穆拉特》大致就是如此:清明,单纯,不可抗拒。
托尔斯泰就是要写一个英雄,或者说他把自己对英雄的全部想象寄于哈吉穆拉特的故事上。与大部分作家以写出人性的复杂为最高目标不同,托尔斯泰在写《哈吉穆拉特》时,不断简化人物性格。在最后一稿中,他删去了诸多可以体现哈吉穆拉特复杂“人性”的细节:他对沙米尔的权势高于自己的嫉妒和恼恨,他对金钱的贪婪,他的自私,他的宗教狂热,他在杀人时的残暴……最后站在我们面前的哈吉穆拉特:勇敢,虔诚,彬彬有礼,眼神宛如孩童,每个女人都爱她;最后哈吉穆拉特被杀,连俄军首领的情妇都要怒斥杀死他的人是刽子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