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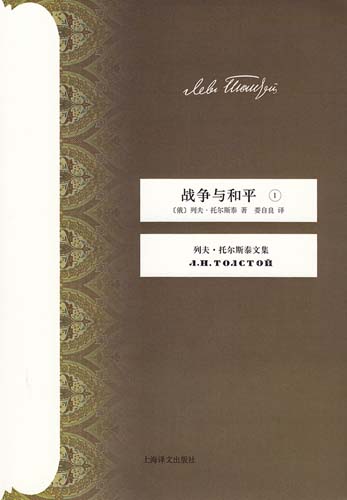 今年是伟大的俄罗斯作家列夫·托尔斯泰逝世100周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特意推出托翁的三部长篇名著《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的新译本,以表达对这位俄罗斯文学巨匠的纪念。其中的《战争与和平》由著名翻译家娄自良根据俄罗斯的最新版本译就。本报现发表娄自良先生的译后散记,以飨广大读者。 今年是伟大的俄罗斯作家列夫·托尔斯泰逝世100周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特意推出托翁的三部长篇名著《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的新译本,以表达对这位俄罗斯文学巨匠的纪念。其中的《战争与和平》由著名翻译家娄自良根据俄罗斯的最新版本译就。本报现发表娄自良先生的译后散记,以飨广大读者。
西方权威推荐书目曾将两位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入书目的前十位,排在圣经以及荷马、但丁、莎士比亚等西方经典作家之后。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在他的《托尔斯泰传》里说:“《战争与和平》是我们时代最恢宏的史诗,是近代的《伊利昂纪》”。这部举世公认的不朽名著反映了一八〇五年至一八二〇年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战争与和平环境中的俄国社会风貌。
托尔斯泰说:“我希望,读者不要在我的书中碰到或寻找我不愿或不善于表达的东西,而恰恰要把注意集中于我想表达,却认为不便细说(限于作品的条件)的地方。”(《战争与和平》,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9月版,1686页)。这是作家对读者的希望,也是对翻译家的希望,而翻译家的学识(中外文造诣以及对外国文化的了解)、才华和努力,以及在这些方面的欠缺,都必然地会反映在他的译作中,因而产生一些很不相同的译本。
译作是否忠实于原著是有标准的,那就是原文。笔者想通过若干译例的比较对译文试加评说,想必慎于选择读物的读者是会感兴趣的。
凡是我的译文均注明页码(以最新的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9月版为例),以便读者查考,而用来对比的译文则并不注明出处,因为我只着眼于译例本身,并无对其他翻译家不敬的意思,我要强调这一点,因为几句译文的正误并不能反映某个译本的整体水平。
一个词的错译:
拿破仑在莫斯科大会战中……
“莫斯科大会战”云云是违背历史的无中生有,而且小说中也写到,库图佐夫早在菲利的军事会议上就不顾俄皇亚历山大一世“断然不准放弃莫斯科”的旨意,力排众议,毅然宣布“我——决定撤退”,对放弃莫斯科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造成这个违背历史的错译的原因只是一个小小的失误:译者可能不知道,俄语Москва这个词也指流经该城的那条河,即莫斯科河,于是硬是译成莫斯科,顾不得历史了。
我译为“莫斯科河战役”,并加底注:
指波罗金诺战役(莫斯科河流经该战区)。(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9月版,1385页)
不言而喻,法国人把波罗金诺战役称为莫斯科河战役还具有鼓舞全军士气的作用:打赢了莫斯科河战役,莫斯科还会远吗?
一段文理不通的译文:
……小高地上驻扎着守桥的俄国炮兵连,高地前是一片辽阔的旷野,时而被斜雨的纱幕遮住,时而豁露出来,远处景物在阳光下像涂过油漆一样闪闪发亮。高地下是一个小镇,镇里有红顶的白色小屋、教堂和桥梁,桥两边都是流动的俄军。多瑙河河湾里有许多船只、一个岛屿和带花园的城堡,城堡四周围绕着从恩斯河注入多瑙河的流水。还看到多瑙河松林覆盖、岩石累累的左岸,以及布满绿色树梢和蓝色峡谷的神秘远方。还有修道院的尖塔,高耸在人迹不到的原始松林里。前面的远山上,在恩斯河那一边看得见敌人的侦察骑兵。
原文炮兵连是复数,几个炮兵连就有十几门大炮和附属的马匹、炮车、弹药车,以及几个炮兵连的全体官兵,岂是“小”(这个字是译者加上去的)高地上能摆布得开的?大军撤退,强敌跟踪,俄军以恩斯河为天然屏障,大桥就在俄军大炮的射程之内,高地脚下就是一座小城,那么何来旷野,而且是一片辽阔的旷野?再看,“多瑙河河湾里有……带花园的城堡”,这么说,城堡是在多瑙河河湾里,怎么又说“城堡四周围绕着”恩斯河的流水呢?“布满绿色树梢和蓝色峡谷的神秘远方”,在神秘的远方能看得到低洼的峡谷吗?还有一些问题不再赘述。产生这些问题主要是由于译者对原文在词义辨析和语法关系的理解上有错误。
文字不多,却有这么多文理不通的地方,对战地景色的描写的审美意义更无从谈起。
试比较不同的译法:
(那是秋季温暖多雨的一天。)掩护大桥的几个炮兵连驻扎在一片高地上,广阔的视野展现在高地前面,忽而斜斜飘落的细雨仿佛薄薄的纱幕,忽而视野开阔,远方在阳光下闪烁的景物历历在目。脚下是小城红顶白屋的民居、教堂和大桥,俄军庞大的部队成群结队地在大桥两侧川流不息。在多瑙河的拐弯处船舶、小岛、恩斯河与多瑙河汇合处碧水环绕的要塞及公园一览无余,多瑙河左岸地势陡峭,松林郁郁苍苍,在神秘的远方,绿意盎然的群峰隐约可见,近处是浅蓝色的峡谷。在仿佛人迹罕至的松林后面,高耸着修道院的尖塔,正前方,在恩斯河彼岸的山上,敌军的几个骑兵侦察小分队遥遥在望。(同上,188-18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