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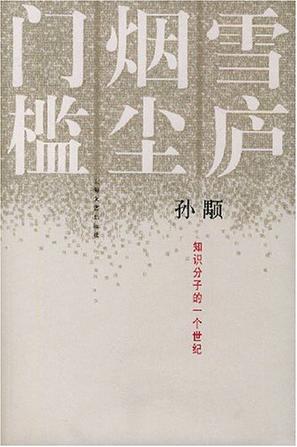 他被称为“丽娃河畔走来的作家”,因为他是华东师大作家群的一员;北京评论家贺绍俊称他为“从《雪庐》走出来的现实主义作家”,或许更鲜明地指出了他的文学特征:把知识分子的命运作为创作的主要标的。他在“文革”期间当知青时就开始写作;他气质儒雅,从他身上能感受到厚重的东西;他关注并涉及的写作范围很广,从文学、文化到音乐、艺术、社会问题,甚至世界时局和金融问题也有所涉猎,他就是原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长、原上海市作协党组书记,孙颙。“五一”前,《收获》将发表他新写的长篇小说《缥缈的峰》,上海文艺出版社也会出版此书。接受采访时,孙颙分享了他的小说创作经历,谈起创作,他说他“从自己写到他者”。 他被称为“丽娃河畔走来的作家”,因为他是华东师大作家群的一员;北京评论家贺绍俊称他为“从《雪庐》走出来的现实主义作家”,或许更鲜明地指出了他的文学特征:把知识分子的命运作为创作的主要标的。他在“文革”期间当知青时就开始写作;他气质儒雅,从他身上能感受到厚重的东西;他关注并涉及的写作范围很广,从文学、文化到音乐、艺术、社会问题,甚至世界时局和金融问题也有所涉猎,他就是原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长、原上海市作协党组书记,孙颙。“五一”前,《收获》将发表他新写的长篇小说《缥缈的峰》,上海文艺出版社也会出版此书。接受采访时,孙颙分享了他的小说创作经历,谈起创作,他说他“从自己写到他者”。
知青生活
孙颙透露,《缥缈的峰》写了四代人,主要是知识分子的命运和追求。从辛亥年间的知识分子,一直写到“80后”。“主要是写当代,把过去作为人物命运的背景和故事发生的缘由。”孙颙说,“写当代生活着眼于复杂和新鲜。例如,把黑客与商战纠葛起来写,几位数学高手卷进了数字时代的焦点。谈及新作,孙颙希望这部小说体现了目前的艺术追求,尽量写出当代生活复杂的人物和丰满的故事,同时努力包含有启示性的哲理。这是他沿着从写自己到写他者迈出的又一步。
孙颙说,多数写小说的人都是从写自己开始,然后进入写自己比较熟悉的故事和人,他最早写的就是自己的知青生活。“1974年时,上海出版社的招待所里面有王周生、我、叶辛、张抗抗等知青写作者,我和王周生从上海农场过来,张抗抗是黑龙江的,叶辛来自云南。我们一开始都是写自己。”孙颙写自己的过程一直延续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
在同行和好友眼里,在农场工作生活的那段时间,孙颙似乎从没有以泄愤或者控诉的态度参与知青文学运动。到农场不久,孙颙就被任命为一个大班的班长。“那时我干活拼命,谁干活拼命就当头。那个时候当干部就是吃苦,我一直当到生产连长。别看我现在文质彬彬,所有苦的活我都能干。”孙颙笑言。1972年,在农场干活的孙颙把身体累垮了。“那个时候是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保尔柯察金为榜样,把自己的身体累垮了,休养了11个月,在那11个月里,我读了大量历史的书籍。”孙颙说,就在那时,他的思想发生了转变,不再是个懵懵懂懂、盲目、头脑发热的年轻人。
1976年初,当时市里想组织一个以批判大官走资派为目标的创作组,领导要调孙颙去。这对他而言是诱惑也是考验。那时大家都是知青,被上面看中就可以离开农村,但孙颙对“文革”和那些新贵已经有批判的意识,他用了“拖延战术”,坚持不去报到,一直拖到“四人帮”粉碎。
冬的回忆
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孙颙告别了他曾经生活过10年的崇明前哨农场,考进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孙颙曾说:“在社会中度过了长长的喧嚣的日子,才明白,宁静的校园生活是何等可贵!”1978年进入大学后,除了上课,他就忙着去图书馆抢座位。“文革”期间,由于没什么可阅读的书,刚进大学的孙颙就日夜泡在了图书馆里。那里有许多“文革”前出版的书,都是他曾经想也不敢想能读到的书。大约半年后,他的心却不安静起来,一种强烈的创作冲动渐渐占据了头脑。他想写一部关于同龄人命运的小说。写他们从狂热参与“文化大革命”,到慢慢清醒过来的曲折的历程。
1978年夏秋之季,在华东师大校园里,孙颙思考着近十几年的风风雨雨,回味自己这代人经历过的林林总总。正巧,那年学校组织学生开展一个月左右的社会调查。白天在市中心调研,趁学业不太繁忙,孙颙每天晚上就回五原路的老家写作。家里有个三四平方米的小屋,狭窄、斜顶,透气依靠直径仅半米的圆形小窗,但这成了孙颙的福地。每天吃过晚饭,他就躲进小屋,至少写5000来字才肯上床。二十多个长夜一天不歇,终于在冬天,第一部长篇小说《冬》诞生了。
这是一部批判“文革”的作品,当他拿着那叠写在粗糙的方格纸上的小说,去找几位文学编辑,询问是否达到出版的水准,得到的答复基本都是:小说具有感人的力量,但是,涉及不少敏感问题,目前出版有困难。面对接二连三地摇头,孙颙有些气馁。
1978年岁末,孙颙意外听到一个消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两位领导韦君宜和屠岸到了上海,他们此行的目的,是想寻找几部“大胆”的新作品。在一个寒冷的雨夜,孙颙忐忑地把小说送到了他们在上海的下榻处。原本以为要经历漫长的等待,却意外在1979年初就收到了回信,信里充分肯定了孙颙的那部长篇小说,并邀请他去北京参加中长篇小说的座谈会。在那次会议上,孙颙认识了王蒙、陆文夫等前辈,并从他们的人生经验中获得了众多的教益。
回到上海,又折腾了大半年,孙颙才终于拿到装订成册的《冬》。这是他的第一本书,是文学道路真正的开始。1988年,孙颙访问美国国会图书馆,尽管那时他已出版不少小说,但那里收藏的他的著作只有《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