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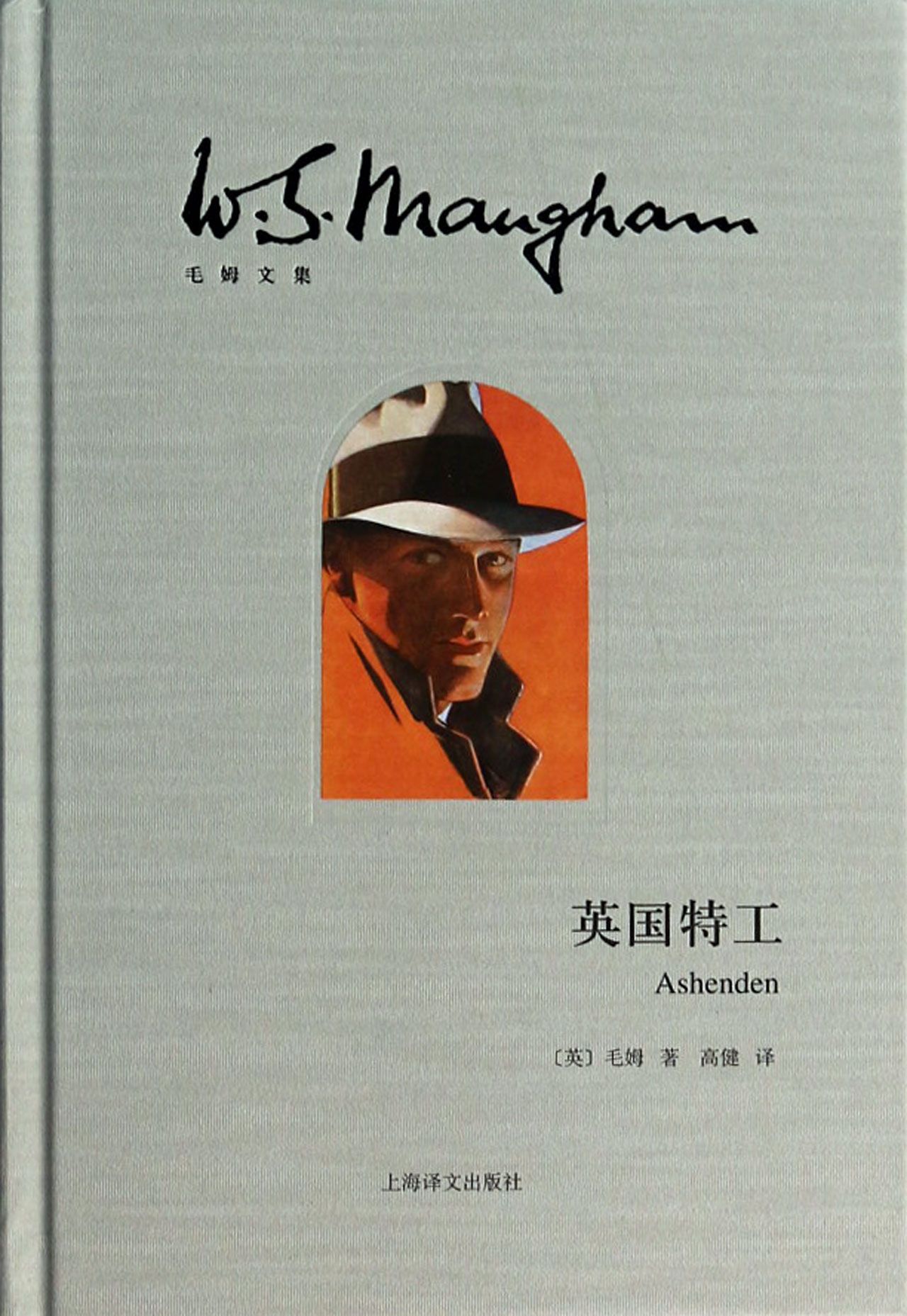 作为二十世纪英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毛姆脍炙人口的作品如同他的名字一样在世界各地流传,比如《人性的枷锁》、《月亮和六便士》、《刀锋》等。关于他的不同版本的传记也屡见不鲜,而他出于高度的爱国主义热情曾经替军情六处工作的历史,却鲜为人知。 作为二十世纪英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毛姆脍炙人口的作品如同他的名字一样在世界各地流传,比如《人性的枷锁》、《月亮和六便士》、《刀锋》等。关于他的不同版本的传记也屡见不鲜,而他出于高度的爱国主义热情曾经替军情六处工作的历史,却鲜为人知。
那段经历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毛姆赴法国参加战地急救队,不久进入英国情报部门,在日内瓦收集敌情;后又出使俄国,劝阻俄国退出战争,与临时政府首脑克伦斯基有过接触。回国述职时,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这一段间谍与密使的生活,后来被他写进了小说中——这部上海译文出版社最新引进的《英国特工》,被誉为“头一部由亲身经历并亲力亲为者创作的间谍小说”。
并不单纯的俄国之行
1917年夏天,毛姆第一次启程去俄罗斯。他对那个在冬季里异常寒冷的国度有着某种莫名的好感,甚至不顾还未痊愈的肺病,仓促前往。
他在海参崴逗留了一天,这并非出于旅行的计划,而是因为他要等同伴们乘坐的西伯利亚列车在24小时之后到达车站。在一顿有伏特加的晚餐之后,毛姆等来了同伴,按照之前的指示,他必须佯装不认识他们,然后一起继续北上,接着向西,最终到达列宁格勒。
事实上,对于毛姆来说,这并不是一次单纯的旅行。
当年3月,俄国沙皇正式倒台,临时政府很有可能被布尔什维克推翻,而后者对于德国来说显然是天然的盟友。作为英国情报部门的高层,威廉·怀斯曼开始策划寻找合适的人选,到列宁格勒去秘密支持温和派孟什维克。他求助于自己的密友毛姆,而当时远在纽约的毛姆也正好可以利用去俄国为美国刊物写稿的借口,成功潜入远东。
一开始,毛姆对这次俄国之行本能地拒绝,但他终于还是没能抵挡那个神秘国度的吸引。
其实对于毛姆来说,间谍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身份。早在两年多前,毛姆就被另一位好友一再提醒:他本人在欧洲的影响以及作家的身份让他几乎具备了一流间谍所需要的全部条件。这个朋友就是一战期间法国和瑞士情报机关的负责人沃林杰爵士,之后他让毛姆以写书和体验生活作为掩饰,去瑞士顶替一名患神经衰弱症的间谍。仅仅维持了一年,首次的间谍生涯最终以毛姆自己的辞职而告终。
这次俄国之行并不那么顺利。在毛姆到达俄国的第三个月,布尔什维克已经成功夺取了政权,他的任务彻底失败。对于毛姆来说,这短暂的几个月,更像是一次负荷实弹的体验。
在他的小说《英国特工》中,主人公艾兴顿是个中年间谍,头发稀疏,害怕秃顶,既不勇敢,也不成功。这个人像极了现实中的毛姆,只不过艾兴顿没有毛姆的两块心病:畸形足和口吃。
他是如此坦诚,坦诚得很难成为一个合格的间谍。
真实的“虚构之作”
“‘事实’乃是个拙劣的小说家。”毛姆在序言中开门见山地指出“此书仅是一本虚构之作”,在他看来一名谍报人员的工作是特别单调乏味的,有些甚至是徒劳无益的。
尽管如此,这本在自己切身经历的基础上写成的《英国特工》,还是相当逼真地描绘出了毛姆的间谍生活。
除了外形特征相像外,小说中有很多情节可以为此佐证。譬如在间谍接头、传递情报、等待英国方面的指示方面,艾兴顿的任务也与毛姆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也写永远不会有人读的报告,可是有一次他在报告中开了一个玩笑,遭到了顶头上司的严厉批评——毛姆在现实生活中也发生过一次类似的情况。艾兴顿还和毛姆一样被派到卢塞恩去监视一个英国叛徒以及他的德国妻子,却不料自己的作用仅仅是充当诱饵。
正是因为真实性,他还曾被迫焚毁了其他未出版的艾兴顿小说——因为温斯顿·邱吉尔阅过手稿后警告他的小说内容违反了政府的保密法。
1928年4月12日的《泰晤士报》文学副刊评论道:“以前从未有人如此清晰地剖析过谍报工作。反间谍工作常常是一些谨小慎微的人或良心未泯的人不愿意做的道义上不可宽恕的工作。”
和其他作品一样,在《英国特工》中毛姆并不是以所谓的惊险刺激眩惑读者耳目,他最感兴趣的仍旧是处在极端情境与危急时刻中的人性。
本书译者高健先生认为,《英国特工》的一些场面也许不是那么轰轰烈烈,但它却是一部完美的书,一部站得住的小说,一部近情合理、可信耐读的和趣味盎然的作品,“既有其事实依据,也不乏想象的发挥,更不违背艺术的与历史的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