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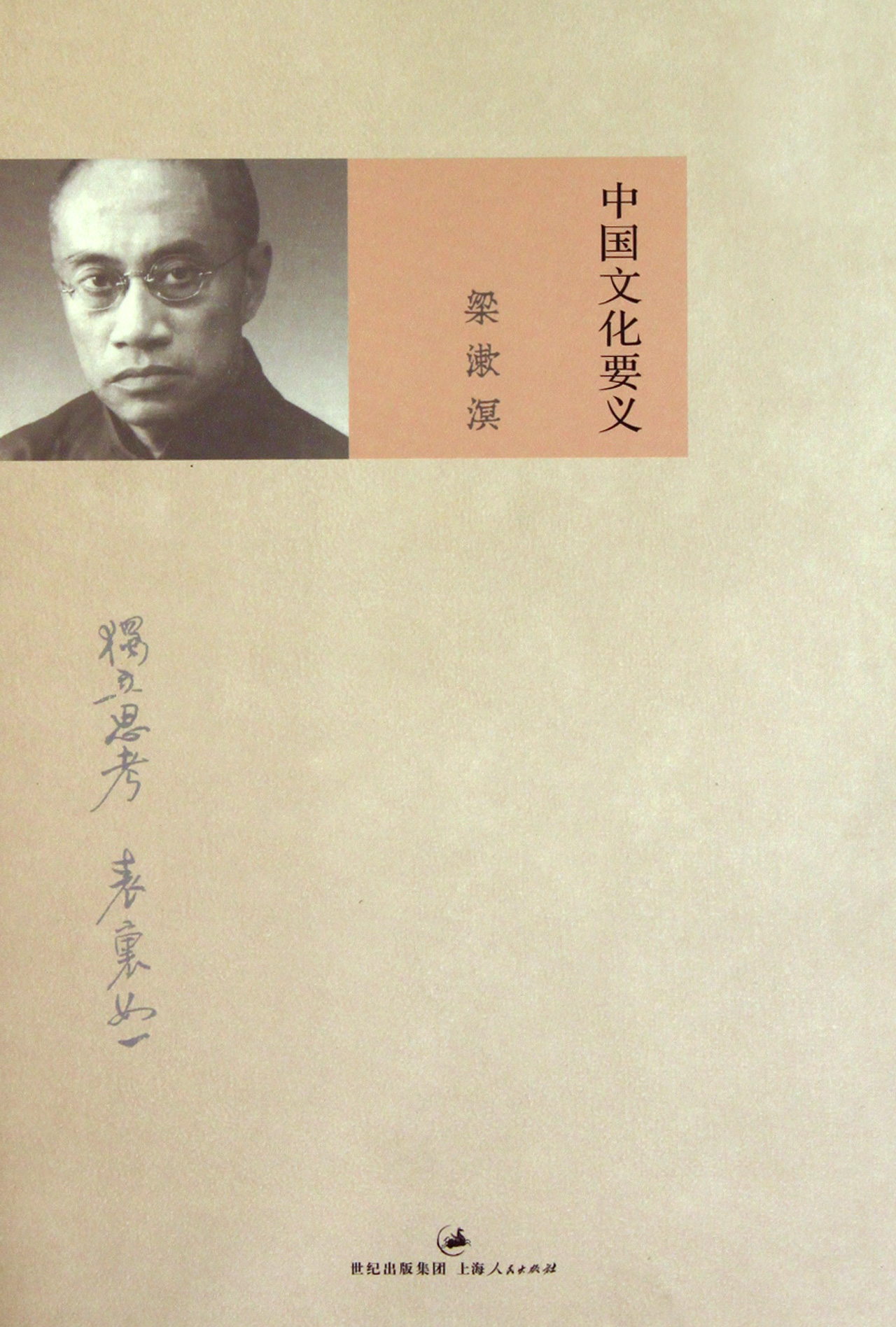 今年10月18日,是“中国最后一个大儒”梁漱溟先生诞辰120周年。梁漱溟是“民盟”的缔造者之一,昨天民盟中央、民盟上海市委和上海社科院在上海社科院联合举办了“文化自省:梁漱溟先生诞辰120周年论坛”,民盟中央主席张宝文、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陈力等几十位民盟成员和学者出席了昨天的论坛。 今年10月18日,是“中国最后一个大儒”梁漱溟先生诞辰120周年。梁漱溟是“民盟”的缔造者之一,昨天民盟中央、民盟上海市委和上海社科院在上海社科院联合举办了“文化自省:梁漱溟先生诞辰120周年论坛”,民盟中央主席张宝文、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陈力等几十位民盟成员和学者出席了昨天的论坛。
多地开研讨会纪念梁漱溟
除了昨天的民盟纪念活动,桂林、北京等全国多地也将举办相关研讨活动怀念大师。10月18日梁漱溟诞辰,梁家后人梁培宽等及数十位专家学者将在北京大学参加由中国文化书院主办的梁漱溟纪念研讨会。世纪文景也将于明年初推出包括《梁漱溟日记》《东方学术概观(增订本)》在内的多部作品。
梁漱溟是20世纪中国极具传奇色彩的一代学人,幼年不学四书五经,而入洋学堂,念《英文初阶》《地球韵言》;曾两度欲自杀,一度想出家,终因哀民生疾苦,叹“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积极入世求解中国与人生两大问题;24岁以中学学历登北大讲坛,教授印度哲学,7年后,主动辞去教职,投身新教育和乡村建设;抗战中,巡历敌后游击区8个月,敌兵围堵,飞机轰炸,数次险死还生,而始终泰然自若;为联合救中国,他发起民主同盟,调查李(公朴)闻(一多)惨案,力促国共和谈,前后奔走8年,被称之为“中国的甘地”;他与毛泽东曾几次通宵长谈,激辩中国道路,1953年因向最高领袖“要雅量”,成为“反面教员”;1971年,他只批“林”不批“孔”,再遭全国性大批斗而不改初衷,傲然宣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文革”被抄家,资料全无,仍笔耕不辍。
与传奇相伴的是种种的误读和误解,梁漱溟不得已,一生都在不断地自我辩白。有人称梁漱溟为哲学家、思想家,他则自辩“我不是书生。我不是学问家。我是一个要拼命干的人”;对被冠以“最后的儒家”称号,梁漱溟自陈“我是一个佛教徒。我的前生是一个和尚”;当众人都在称赞他敢于触犯“龙颜”的骨气时,他却自我反省“态度不好”“满身旧习气”。
梁漱溟和毛泽东的分歧与一致
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几次通宵长谈激辩中国道路,这段经历在他传奇的一生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上海社会科学院思想文化研究中心秘书长马驰在昨天的发言中说,后人了解梁漱溟,莫过于当年在延安,他与毛泽东就“如何建设一个新中国”进行辩论,针对西方社会“个人本位”、“阶级分化”的特点,他提出了更加符合中国社会现实的“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观点。毛泽东十分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作用,梁漱溟不同意的正是这一点。“他认为,中国社会与外国社会不同。在历史上,外国的中古社会,贵族与农民阶级对立鲜明,但中国的中古社会贫富贵贱不鲜明、不激烈、不固定。当时两人相持不下,谁也没有说服谁。时至今日,再以社会发展现实状况来看,似乎情况更接近梁漱溟的分析。”马驰说。
梁漱溟的重要思想集中体现在他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发表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及在国共两党激烈冲突时出版的《中国文化要义》等重要著作中。马驰认为,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基于他对中国社会实际的观察与研究,提出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以此否定阶级斗争理论,认为自己多年来进行的乡村建设才是中国的惟一出路。一直到1980年,梁漱溟与艾恺对谈的时候,他才不再坚持“向东走”,不再反对“向西走”,相反,连他自己都有到欧美走走的意思。在对自己先前著作进行评价时,梁漱溟也不再像先前那样自负。
梁漱溟认为“中国非一般国家类型中之一国家,而是超国家类型的”。马驰认为,按照梁漱溟观点,中国与其称为国家,不如将其作为以伦理关系为纽带,以伦理情谊为主要维系手段的“文化共同体”。在社会与个人相互关系上,梁漱溟认为,中国与西方社会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的特殊性就在于从家庭出发而不止于家庭,是以伦理关系组织社会。“梁漱溟在这里对中国社会结构或特征的把握是偏颇的,甚至是错误的。他的致命伤是以偏概全,用一时、一地的个别现象代替了普遍现象。又由于他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夸大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而否认了人类社会历史存在的普遍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