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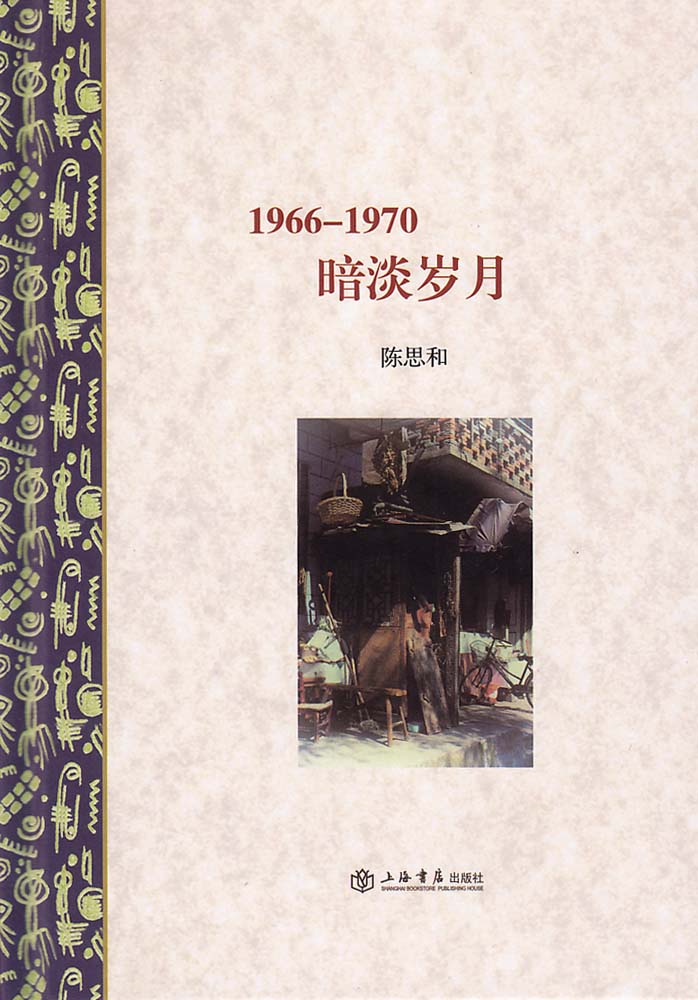 陈思和的回忆录《1966-1970:暗淡岁月》,曾想用名“土中蛹”,意谓“埋藏在泥土里暗无天日,却吸收了土中营养而慢慢形成的虫蛹”,以影射自我生命的蜕变。这是一个有趣兼有意味的比喻,易引起多元的联想,如有人打趣说是不是可以当作宅男的极好称谓,自然这是以今视昔,过于单纯,未考虑时代的因素。而陈思和的“暗淡岁月”纷纷扰扰,一个少年的成长遭逢枝节歧出,土中之蛹时有迷茫,难辨方向,但终究于暗地静默汲取养分,貌似蛰伏,却有隐性的活力,等待着其后的“结茧、蜕变和羽化”。 陈思和的回忆录《1966-1970:暗淡岁月》,曾想用名“土中蛹”,意谓“埋藏在泥土里暗无天日,却吸收了土中营养而慢慢形成的虫蛹”,以影射自我生命的蜕变。这是一个有趣兼有意味的比喻,易引起多元的联想,如有人打趣说是不是可以当作宅男的极好称谓,自然这是以今视昔,过于单纯,未考虑时代的因素。而陈思和的“暗淡岁月”纷纷扰扰,一个少年的成长遭逢枝节歧出,土中之蛹时有迷茫,难辨方向,但终究于暗地静默汲取养分,貌似蛰伏,却有隐性的活力,等待着其后的“结茧、蜕变和羽化”。
少年时期的隐忧心理与精神的成长,是陈思和在回溯往事时有意梳理出来的。在那个时代,一个有“历史问题”的父亲对家庭成员的影响可想而知,而于陈思和来说,这是内心的隐秘,因为父亲远在甘肃兰州支援建设,其隔离审查未为上海方面得知。陈思和说,“如果别的人知道我父亲还在隔离审查中,我就可能成为那个时代的另类人。现在虽然没有把这个秘密公布出来,但内心恐惧依然存在。”这,就是隐忧了,此种内心折磨显然影响了陈思和的精神成长,“我与时代的主流不自觉地保持了精神上的疏离”。而“文革”岁月,从外在的“蓝蚂蚁”装扮,到精神上的强力统一,都表明了笼罩全体的集体意志,在这种情状下,不求同即为异类,于所有人而言是不言而喻的。人性本身有根深蒂固的从众心理,在特殊年月里尤变本加厉,而少年陈思和因隐忧的存在,在集体意志与疏离之间徘徊、煎熬,不能自已,也正是于此过程中,个人有着艰难的成长。他自言,第一次阅读巴金的小说《憩园》,对落落寡欢的杨梦痴产生出“难以言状的同情”,显然与其时的心境息息相关,同样的落寞,同样的与社会主流的不适,让少年时的他心有戚戚。及至后来,陈思和走上学术研究道路,起首即做巴金研究,写出《人格的发展——— 巴金传》等著作,与他少年时的经历有否草蛇灰线的微妙脉络?这是对学者之学术生涯追根溯源中值得探讨的。
“文革”中乱象频仍,批判不断,炮火猛烈,但这些批判收到的效果有时却微妙得紧。如1968年,高层欲收拾过于混乱的局面,开始有组织地发文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潮”,将诸多混乱因素打包归入“无政府主义”,且上纲上线,将之描画得漆黑一团。少年陈思和所在的中学,自然也要接受教育,大张旗鼓,灌输进学生们的头脑。他还回忆当时上海有批斗巴金的大会,有人将巴金青年时期写的关于“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展示出来,以示其一贯反动。这一切反而激起了陈思和的好奇心,迎来这般抨击的洪水猛兽到底是什么真面目?这也成为他之后学术研究中的重要一环,有着如此的种瓜得豆的效果,恐是当年那些批判者意想不到的。对少年陈思和影响深远的另有一部书———《水浒传》,也是在“文革”时期被作为反面教材大肆批判的,不过在外祖父的文本细读“辅导”下,小说与现实的叠加冲突总是令他疑惑不已。如外祖父说,“晁盖是个盖啊,宋江是口缸,盖子揭掉了,缸才能出头啊”;而在梁山泊排座次时,大刀关胜的功劳远不及林冲,却排在林冲之前,“宋江这一手,与当年白衣秀士王伦要引进杨志牵制林冲的用意是一样的”。民间的解构能力不能小觑。少年陈思和在如此的影响下,外在的时光虽暗淡,不过土中蛹可获致的营养却不至于太贫瘠了。
陈思和生于上海,长于上海,上学和工作几乎都没离开过这个城市,对其文化之流变脉络一直关注有加,而暗淡岁月中海派文化的嬗变自然有其亲身体会与深入研讨。上海自近代就有白相人文化的传统,也即流氓文化,如黄金荣、杜月笙之流,所谓“大阿哥一句闲话,就搞定上海”,这是殖民地文化的特色,是一种“上下合流的文化主导”。这一海派文化根深蒂固,并不因时代的改变而消失殆尽;“文革”动荡伊始,即有王洪文、陈阿大之流一哄而上,占据要津,成为祸国殃民的“海派英雄”,白相人文化在这个城市的根基深厚,可见一斑。而这几年颇流行的海派清口,津津乐道的“打桩模子”,其由来正是“文革”造反组织“上体司”的打手们,不知有多少喜听清口的上海人知晓这个不光彩的来源?另有如“扎台型”、“有腔调”、“朋友帮帮忙”等,均来自各个时期的流氓切口,如今呢,在沪上的公共语言中似乎煞是流行。或许作为一种流行文化也没什么,但放远眼光从长时段看海派文化,总觉得有些不妥,是不是忘记伤疤太快了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