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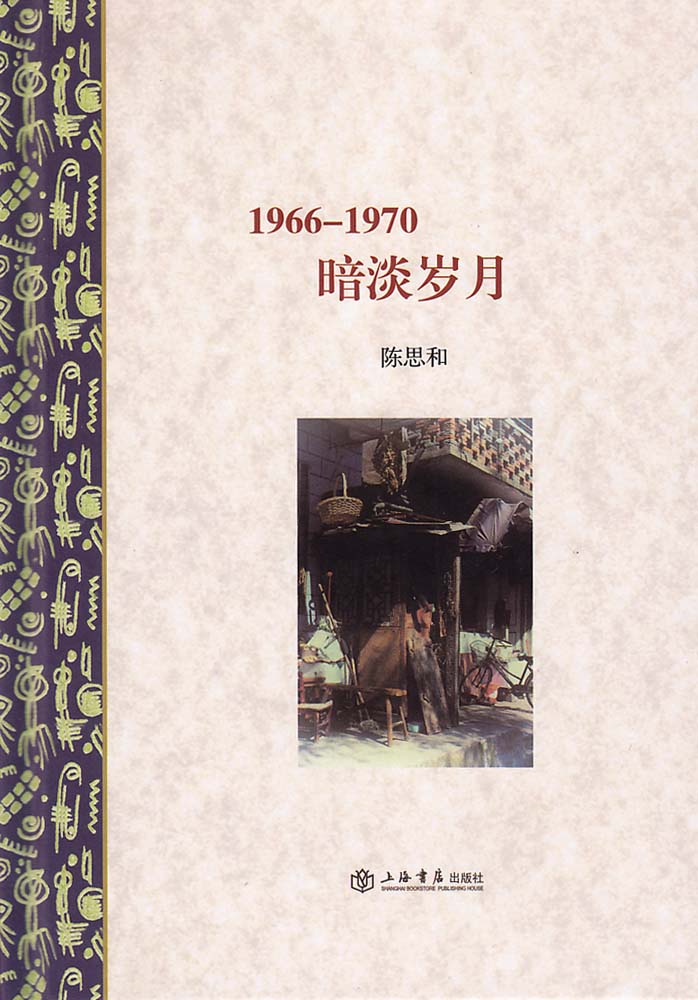 陈思和自传性质的新书《1966-1970:暗淡岁月》中代序部分《上海的旧居》,实在可以称得上是一幅珍贵的旧时代上海建筑文化地图。作者在上海居住了近六十年, “记忆像一条回到巢穴的狗那样耸着鼻子拼命地追寻过去岁月的遗迹”,旧时代的大舞台剧场、典型的石库门房子、石库门里窄长的木楼梯等,重新拼接出了旧上海的模样,具有了一种居民博物馆的意义。当然,这里绝不是对上海旧建筑风貌的纯客观介绍,而是附着了太多的家族记忆。 陈思和自传性质的新书《1966-1970:暗淡岁月》中代序部分《上海的旧居》,实在可以称得上是一幅珍贵的旧时代上海建筑文化地图。作者在上海居住了近六十年, “记忆像一条回到巢穴的狗那样耸着鼻子拼命地追寻过去岁月的遗迹”,旧时代的大舞台剧场、典型的石库门房子、石库门里窄长的木楼梯等,重新拼接出了旧上海的模样,具有了一种居民博物馆的意义。当然,这里绝不是对上海旧建筑风貌的纯客观介绍,而是附着了太多的家族记忆。
之所以选择“1966-1970”这个年份,于作者,那是他整个青少年时期转型和完成的过程,其间有不少对少年的他产生了足以影响以后的精神成长和人生轨迹的事件。当然,这个年份自然昭示着另外一个回避不了的事件——“文革”。这个给当时的全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事件自然成为整本书讲述的主题。作为亲历者,作者回溯了他所经历的“文革”, 那个乱哄哄的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不几天的混乱岁月。
虽写“文革”,但作者并没有流于愤怒的控诉,而是以少年的眼光和经验回顾了那段亲身经历,亦加入不少反思。作者并不讳言自己在“文革”中加入红卫兵的经历,在唯成分论的时代填表格时将父亲的“店员”身份改为“干部”、“工人”,反省自己当时并没有真正关心审判的是什么人,而只是借一个理由可以到市区游玩,对受迫害人的同情也因与己关系远近而不同……再次回视过往那段不成熟岁月,作者在文中清楚表达的自我反思难能可贵。
与同时代反思“文革”的文字相比,作者的学者身份无疑能够帮助加深对十年浩劫反思的学理与深度。如作者如此分析“文革”中民众的从众心理:“一切人都要在混乱中把自己融入集体的意志,才能得到某种残剩的安全感。个人微不足道,从众才会使自己变得强大起来,所以个人要保护自己就必须先从主观上泯灭自己,把自己融入到集体无意识中去”,并用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来解释处于性骚动期的男女红卫兵以“革命”的名义释放里多比的狂欢与压抑。分析上海造反派时,不但发现了与巴黎公社的相似点,并且进而将这种派系斗争与近代上海的租界、巡捕房、黑社会势力、“白相人”等联系起来,“大阿哥一句闲话,就搞定上海”。这种当年连胡兰成都羡慕不已的具有上海殖民地文化特色的白相人文化,被作者拿来与当时王洪文治下的上海境况做对比论述,深刻剖析了白相人文化如何在统治者与民众间寻求平衡并相互利用,并用黄金荣、杜月笙比王洪文、陈阿大之流。这样的反思批判便找到了一个更为宽阔的视野,具有了浓厚的地域文化特色,学理的深度和广度也得到进一步拓展。
当然,作者对“文革”的回忆也时常充满着“悖论”,“文革”不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凝固的铁板一块,而是在难以言说的苦难背后,也有让人得以喘息的温情与可资汲取的能量。即使当时上海已经乱得不能再乱了,但有些规章制度还是很人性化的,如商品奇缺时每个国营菜场都设有糖尿病专摊,糖尿病人可以凭医院证明轻易购买到比平常家庭多几倍的食品;“批判电影”中,展现出了一个与粗暴的现实世界完全对立、澄明而丰富的电影艺术世界,作者借此接触到了现代文学的丰富营养;鲁迅的书在被统治者利用的同时,其中蕴含的批判和怀疑精神也在知识匮乏时代启迪着青年人……
作为学者的陈思和,不仅能很精准地直击事件的关键之处,而且语言能够在严肃严谨与轻松幽默之间找到巧妙的平衡。阅读这本书,在我看来算得上一种奇妙的阅读之旅。也许有人会因为书名中的“暗淡”字样而担心里面的文字会不会过于“暗淡”。于我,非但没有觉得压抑,反而有种隐秘的快感。这也许归因于书中不时出现的强大的民间智慧。不得不说,我实在太喜欢作者的外祖父这个可爱的老头儿。外祖父与热切追逐时代主流的父亲不同,他一生都在与社会时代主流保持着近乎偏执的警惕和疏离,往往能预见一些重大政治事件的走向,但却对外界保持绝对的隐忍与沉默……外祖父隐喻了瞬息万变的社会风潮背后朴素的民间智慧,是道家思想在群魔乱舞时代对人性的一种滋养。
我相信,历史从来未被遗忘,它只是以各种形式,长存在于人们的记忆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