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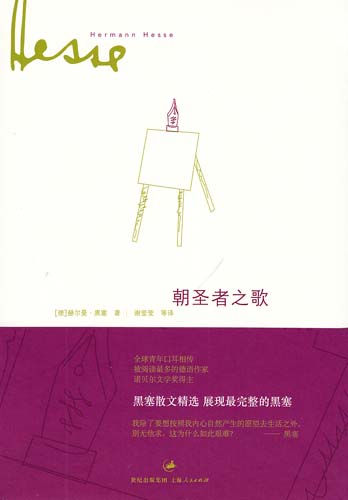 “我谴责并诅咒你们的战争,但是我不想这样活着,请把我打死吧!”黑塞在1933年一封致友人书信中写道,谈的是自己1914年时的想法,那年他已经很有名望,德国上下都希望他能在此刻出来,为即将出征的军队、为武装起来的国家打打气。8月,黑塞应征加入德军,不过身份是“战争志愿者”,动机则是一种文人式的赌气:朋友们都上战场了,我却坐视不顾……好吧,我也豁出去了,横竖是个死。 “我谴责并诅咒你们的战争,但是我不想这样活着,请把我打死吧!”黑塞在1933年一封致友人书信中写道,谈的是自己1914年时的想法,那年他已经很有名望,德国上下都希望他能在此刻出来,为即将出征的军队、为武装起来的国家打打气。8月,黑塞应征加入德军,不过身份是“战争志愿者”,动机则是一种文人式的赌气:朋友们都上战场了,我却坐视不顾……好吧,我也豁出去了,横竖是个死。
但一年之后,黑塞正式形成了自己的反战立场,他的理由与众不同,他认为,文学艺术有固有的界限,既然要做艺术家,就不能去干那些份外事。1915年8月,他在一封致丹麦作家斯文·朗格的信中写道:“我觉得在文学上适应战争是不会成功的,我希望德国能……首先以和平的艺术,进而通过使超国界的人道主义成为现实而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这封信一公开,立刻为他招来了口诛笔伐。
《朝圣者之歌》收录了黑塞的一些散文随笔,其中最后一篇,是1948年致马克斯·布罗德的一封信。布罗德是卡夫卡的挚友,由于他的坚持,卡夫卡的小说才免遭火焚而与世人见面。1948年5月,以色列宣布独立,第一次中东战争旋即爆发,巴勒斯坦地区一片战火,布罗德希望黑塞能出面做点什么,好引起国际社会介入,以免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的文物,特别是那里保存的卡夫卡未刊遗稿受损。黑塞接信后,回了一函表示拒绝:这不是文人职责范围内的事,他说,因为“我们的国度注定‘不属于这个世界’……世界舞台没有我们参与的余地”,这块地盘“我们不能用,也不允许用……只有让给他们”,让给那些政治人物。
布罗德的要求合情合理,黑塞的反应大可争议:他的反战立场,经过了两次大战之后,现在似乎固化为一种消极遁世的姿态了。在这封信的末尾,黑塞表明他很知道自己将要承受的名誉风险:“不深入探究的人一定会怀疑我是个爱梦想的艺术家,怀疑我认为艺术和政治没有任何关系,认为接触到险恶的现实会破坏情调或弄脏自己的手,因而整日躲在审美的象牙塔里。我知道,在您面前,我无需就这一点为自己辩护。”一年之后,他在一篇散文中又一次写到:“每一天都在向我提出要求,要我去适应这个世界,就像大多数人所做的那样……”
人们管黑塞叫“最后一个浪漫骑士”,但是他的漫长人生覆盖了两场很不浪漫的世界大战,在一战中,他的消极表现激怒了德国人,到二战时,他的书又被纳粹大批烧毁、查禁,他那些玄味十足的小说、随笔,那些清新亮丽、阳光普照的风景散文,在国家社会主义者的眼里无异于麻痹人民意志的“靡靡之音”。但是,人们总是希望知识分子多一些现实担当,虽不至于悬壶济世,至少不可漠然于人间疾苦,而黑塞在一战过后没多久就移民去了瑞士,当他的德国同胞在忍受魏玛的煎熬时,他却躺在苏黎世的温泉疗养院里,琢磨下一部境界高远的作品。黑塞很清楚,在这个问题上他必须付出代价。他在晚期的小说《玻璃球游戏》中塑造了一位投身于超卓学问的玻璃球游戏大师,此人就如同黑塞本人的另一个自我,替他承受着来自世俗的质问:你凭什么自以为在从事高贵脱俗的事业?凭什么不事农桑、不懂稼穑,而要求那些胼手胝足的劳动者来养活你们?
在《朝圣者之歌》里所收的几篇时政类文章中,黑塞多次发表了自我辩护:“我相信,大概没有一个诗人或文人,今天在一时的怒气之下所说所写的东西,将来会成为他全集中最好的作品。”这几乎是把从左拉到萨特、到加缪、到雷蒙·阿隆以及西蒙娜·德·波伏瓦等等这一支法国“介入文学”传统一杆子打翻了。加缪是个标准的感官主义者和现世主义者,他在二战结束时发表《致一位德国友人的信》,指责德国人痴迷于英雄主义,而忘了“幸福才不易得”;相反,黑塞对德国式英雄主义的指责是出于另一个纯然形而上的理由:这种盲目的情绪会玷污真正的德意志精神——以歌德为代表的德意志精神,它并非独属于一个民族的珍宝;它是世界主义的,是“人类总体特性带给他的喜悦”。
其实,这个矛盾在黑塞看来,无非是个人追求不同罢了,有人向外扩张,就得有人向内掘进。黑塞的散文中有一股很容易识别的灵修味道,拿些片断出来,跟克里希纳穆提等印度灵修大师的文本比比还似曾相识。灵修并不深奥,不需耗费大量的理性去推敲理解,甚至也不神秘,它诉诸的是个人的禅定,让自我彻底地朝向内在。黑塞散文中经常出现“内观”一词,他认为,像自己这样的艺术家就该是从事这一行的,而这个选择的高尚性、超越性价值都是不容置疑的。“我们特立独行者、我们沙漠的布道者,我们并不站在一旁淡然视之,我们也不以为自己高高在上——不过我们认为,只有人的灵魂中发生的事才称得上‘伟大’。”(《世界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