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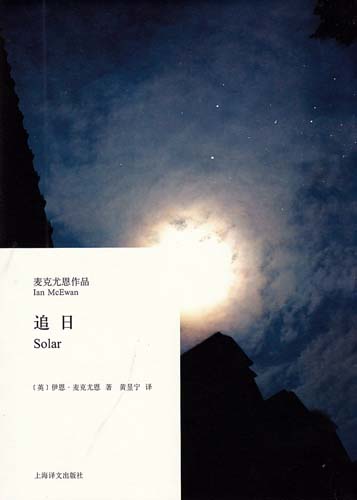 任何一个作家都有“变脸”的渴望,因为这是自己突破藩篱、挣脱瓶颈的明证所指,伊恩·麦克尤恩自然也不例外。作为一个书写闭环境遇中奇情奇事而成名立万的小说家,麦克尤恩意欲撇清自我早期创作形态的努力,在近年的写作中愈发彰显,其《追日》显然是野心之作,亦为“炫技”之作。一个文学作家敢于触碰科技题材,且并未避实就虚、仅仅将其作为背景板,而是“高度仿真”,“经得起专业级别的推敲”,这是须下大功夫的。麦克尤恩的特点在于,他肯做这样的功课,且做得来,完成得漂亮,如果有“作家的自我修养”课程,他是可以作为典型上线的。当然,文学作品的好坏,题材固然是一重要环节,而人物形象塑造、内涵挖掘的力度如何,更具有拨开云层见日头的最终效应,这也是麦克尤恩亟亟注目之所在。 任何一个作家都有“变脸”的渴望,因为这是自己突破藩篱、挣脱瓶颈的明证所指,伊恩·麦克尤恩自然也不例外。作为一个书写闭环境遇中奇情奇事而成名立万的小说家,麦克尤恩意欲撇清自我早期创作形态的努力,在近年的写作中愈发彰显,其《追日》显然是野心之作,亦为“炫技”之作。一个文学作家敢于触碰科技题材,且并未避实就虚、仅仅将其作为背景板,而是“高度仿真”,“经得起专业级别的推敲”,这是须下大功夫的。麦克尤恩的特点在于,他肯做这样的功课,且做得来,完成得漂亮,如果有“作家的自我修养”课程,他是可以作为典型上线的。当然,文学作品的好坏,题材固然是一重要环节,而人物形象塑造、内涵挖掘的力度如何,更具有拨开云层见日头的最终效应,这也是麦克尤恩亟亟注目之所在。
对学术名衔的追捧,看来不单在国内盛行,置于任一国家都有普遍性。《追日》中,迈克尔·别尔德年轻时曾拿过诺贝尔物理学奖,自此躺在功簿上,吃了几十年老本,照样有人买单。不过别尔德的家里可不怎么太平,结了五次婚,从来逍遥的他被第五任太太戴了个很大的绿帽子,从此事故不断,恰合祸福相倚的辩证道理……
麦克尤恩以迈克尔·别尔德为作品的主角,未免不太讨喜。此人自私、无责任心,又是饕餮之徒,且好色无厌,除年轻时用过一阵子功,灵光一现想出一个新的理论,拿到诺贝尔奖外,完全成为学术界的大花瓶。而吊诡的是,如此的人物承担了“追日”的重任,成为“拯救地球”的补天者,是否反差大了些?麦克尤恩在此意欲摹写的,已不是一般的参差之别,而是强烈的反差,外观光鲜的补天者,其真实状态却是在尘埃与泥泞中打滚儿不休,让人情何以堪?理想主义的喜剧性表达,莫过于此了。
别尔德的理想主义,总是令人疑窦丛生。先是在主管的研究所信口开河什么风力涡轮机蒙事,结果全班人马和资金都陷了进去,白白耗费人力物力。没想到一场无妄之灾,让他获得意外身死者的遗物,从中发现了科学上的创新点,开启其理想主义之门。而这理想主义的实践,原初即与剽窃他人科研成果紧密挂钩,怎能不让别尔德成为不折不扣的“尴尬人”?而这尴尬人偏偏要做崇高的事体,誓将“补天”行径进行到底,人性的复杂已是分不出什么色调了。
据说麦克尤恩写作《追日》的想法起源于自己的一次北冰洋之旅,那次各国科学家和艺术家一同参加的考察旅行给予他极大启发,许多场景被照搬进小说里。一边是全球变暖、人类生存、拯救世界的宏大目标,一边是更衣室里愈来愈混乱的状态,更多的大衣、手套和靴子被有意无意地“偷窃”,更多的人愤愤于自己的东西不翼而飞的的同时,转手顺走别人的,麦克尤恩借别尔德之口说,“他们怎么才能拯救地球呢——假设它真的需要拯救的话,对此他深表怀疑——地球可比这更衣室大好多好多啊。”而我们可以想见,地球虽比更衣室大好多好多,但意欲出发拯救它的人们终究要从更衣室里起步呢。
不妨说,别尔德的“更衣室”固然混乱不堪,可他的“补天”愿望却不是虚假的。且在实际行动中,他已行百里中的九十,虽因潜伏的危机在最后关头爆发,止步于此,但其为自己的理想之决心与行动力还是大家都看到的。在此,别尔德的小丑形象与堂皇的补天者行为交织在一起,令人难以梳理出该持什么样的情感对待之。这是麦克尤恩的狡黠处,也是其老谋深算的地方,世间本少黑是黑、白是白单色的东西,他只是将参差之态拉扯得更大一些,如此,世态与人性是变得更分明了,还是更模糊了?但凭观者自己的体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