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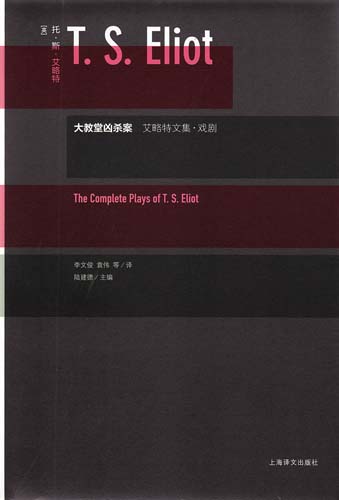 T.S.艾略特(1888-1965)曾经将自己概括为“文学上的古典主义者、政治上的保皇派、宗教上的英国国教高教会派”,这三个标签简明易懂,并不需要详细说明,因为它们都指向保守主义。他的保守主义实际上又根源于他思想深处相当严格的“确定论”,以及个性上过于诚实的自我意识,他不会轻易地接受混沌、朦胧和不可知的事物。从这方面说,保守主义代表着他与崇尚自由的现代价值体系保持的距离,一个不亢不卑的距离。 T.S.艾略特(1888-1965)曾经将自己概括为“文学上的古典主义者、政治上的保皇派、宗教上的英国国教高教会派”,这三个标签简明易懂,并不需要详细说明,因为它们都指向保守主义。他的保守主义实际上又根源于他思想深处相当严格的“确定论”,以及个性上过于诚实的自我意识,他不会轻易地接受混沌、朦胧和不可知的事物。从这方面说,保守主义代表着他与崇尚自由的现代价值体系保持的距离,一个不亢不卑的距离。
他的批评在一种谦逊的外表下包裹着不容反驳的结论,非常地言之有物、条理分明和实用有效。任何读者通过他的批评都能学会理解一首诗或一篇散文——哪怕是自己不喜欢的诗或不喜欢的散文。他的批评很少掺入个人感情,他为诗人分类用的是“大和小”,而不是喜欢和厌恶。他在批评上的功绩就在于建立起一种非常客观和可靠的鉴别标准,使现代批评迈上能够对一切进行量化的轨道。
他建立标准方法首先在于形成一套实证科学式的分类体系。比如,对于诗来说,除了通常的比较粗犷的分类:叙事诗、史诗、抒情诗、颂诗等等,他发现一种更有价值的分类,这个分类针对的是诗的材料,比如意象、行为、思想或灵感结晶、事件、瞬间的情感体验,以及景色中的自然万物。
诗人运用的材料越可靠,诗越有客观意义,也就越有价值。而且鉴别一首诗的价值,只要把材料相同的诗放在一起比较,看此材料是否得到充分运用就一切了然了;同样如要在诗人之间做比较,只要比较他们作诗常用的材料,以及运用此材料的常用手法也可以了。
艾略特的基本诗学就是诗的材料学,基于这一点,我们就更清楚他在《批评的界限》一文中给批评所下的定义:“他们能让我去看我过去从未看到过的东西,或者只是用被偏见蒙蔽着的眼睛去看的东西,他们让我直接面对这种东西,然后让我独自一人去进一步处理它。在这之后,我必须依靠我自己的感受力、智力以及发现智慧的能力。”
有一类诗让艾略特特别困扰,这就是诗人斯温伯恩的诗。斯温伯恩的诗似乎找不到确切的材料,既没有形象,也没有思想,它用的都是浮泛的词,大多是在抒发情感,但是这种情感又从来不具体,“诗也不是通过浓缩而是通过扩展才显示自己的力量”(《诗人斯温伯恩》)。艾略特认为斯温伯恩的诗是一种奇怪的诗,并认为它们得之于语言,自成一体,只有声音又没有音乐性。面对这种诗,艾略特也只能得出这种奇怪而空泛的结论。
艾略特诗学上最大的成就是重新定义玄学诗,将其看做是英诗传统的主流,并用它们重新描述和预测英诗的走向,此举在英美之间激发了大量的批评思潮和诗歌流派。玄学诗的材料是一些确定的观念或偶然的灵感,它们来自于对周围世界感知的综合;这些材料分布在诗句中间,甚至还可能藏在句子之间的空白处,它能让读者感知到某种“机智”(wit)。
这种诗的特点在于能够运用最简单纯净的语言重现一种朦胧的、混沌的思想状态,而诗人的才能在于将这种朦胧的、混沌的思想状态表现得像真理一样确切、不可分割。这是一种巧妙处理不确定性的方法,而且唯有通过诗的强大说服力才能加以把握。
艾略特是从波德莱尔 《恶之花》 里的两句诗懂得如何运用自己手里的材料的,“拥挤的城市!充满梦幻的城市/大白天里幽灵就拉扯着行人!”这两句诗将“卑污的现实和变化无常的幻景合二为一”,其运用的材料是一个凝练的都市即景,这种材料也是艾略特每天都能体验到的东西,个人的体验再加上时代的思潮(迷惘的一代和虚无主义的),就构成了他的诗的形体和灵魂。
当然,不能说艾略特的诗全是由这种材料构成的,只能说这种材料在他的诗里得到了较为纯熟的运用,他的名诗《荒原》是这样的,他后期的诗《圣灰星期三》则是充满宗教虔诚意味的玄学诗。他最能得到大众喜爱的《老负鼠的群猫英雄谱》 使用的材料则是活灵活现的猫性。在这首诗里,艾略特的保守主义被小猫高贵、独立、自由的精神一扫而空,一个个性格迥异的猫被他描绘得妙趣横生,根据这组诗改编的音乐剧(由作曲家韦伯改编)被称为最成功的音乐剧。
艾略特的诗中那种迷惘的文学思潮已经被现代信息风暴吹散到图书馆的角落里,他作诗的材料当然仍然可以用,但要推陈出新才能产生当代人的共鸣。他的批评比他的诗更有生命力,在提高诗者的鉴赏力和教导新作者如何处理手里的材料方面,仍然像纲领性文件一样有效。译文社这次出版的文集包括一本诗集、一本诗剧集、三本精选的批评集,后者尤其值得收藏查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