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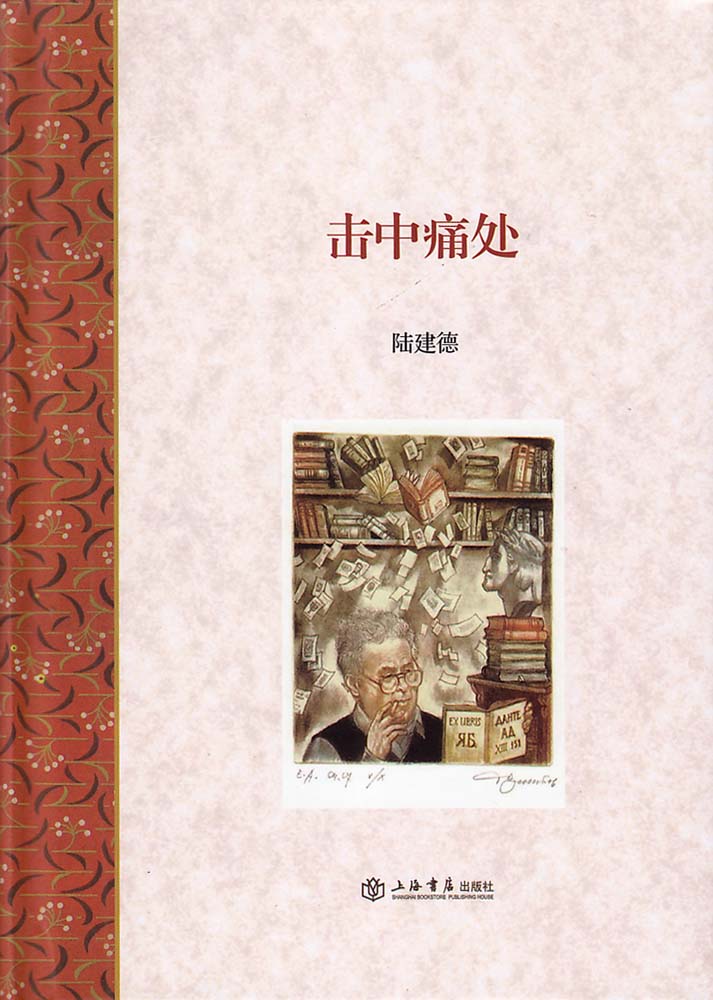 萨义德说,出入于不同的文化之间是一种福分。陆建德说自己对此深有同感。出入于英语与中文两种文化传统之间,陆建德感慨另一种传统带来的参照眼光意义重大。他记得在复旦读书的时候读奥威尔的《动物农场》,对小说里的老马生出同情,“我那时已经二十好几的人了,心里有点奇怪,怎么自己会被动物的命运打动?那是一种新的感觉,为此我永远感激奥威尔。” 萨义德说,出入于不同的文化之间是一种福分。陆建德说自己对此深有同感。出入于英语与中文两种文化传统之间,陆建德感慨另一种传统带来的参照眼光意义重大。他记得在复旦读书的时候读奥威尔的《动物农场》,对小说里的老马生出同情,“我那时已经二十好几的人了,心里有点奇怪,怎么自己会被动物的命运打动?那是一种新的感觉,为此我永远感激奥威尔。”
英伦文化深深影响了这位学者。给他打电话写邮件,陆先生总是温文尔雅、礼貌周全,英伦绅士的风度,但一进行起本行的文学批评,陆建德也毫不含糊。“文学批评从来不是单纯的文学批评。”在陆建德看来,文学批评家同时怀抱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是从约翰逊博士以来的英国文化传统。他说,他写的很多文章,谈的看起来都是英国、美国这些西方国家的事,但其实心底里想的都是中国的现实处境。
从社科院外文所到文学所,陆建德从社科院大楼的十一层搬到了七层,但两个文化之间彼此参照、探究的步伐一直不曾中断,这几年反而更深入地进入到近代史的研究。一个人应该出入于不同文化之间,陆建德的一个比喻是,就像一棵大树,根系能够自由伸展到其他地方去,汲取不同的养料,而不是局限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面。
复旦求学与留学剑桥
南都:在你的文章中似乎很少见到你回忆过往读书求学的经历,你应该是78级复旦大学英语系的毕业生?
陆建德:对,我初中毕业后在社会上待的时间比较多一些,1978年进校,1982年毕业,后来就考试,1983年就去剑桥留学了,经历比较简单,1990年博士毕业回国,到社科院外文所工作。进大学之前有一些自己读书、学外语的经历。
南都:在复旦的时候陆谷孙先生也教过你?
陆建德:陆谷孙先生是我的老师辈,那时候他教的课非常受人欢迎,可以说人满为患,我去听过。陆先生讲课很投入,有迷人风度,英语词汇量极大,口语流利,善用短语,可惜他没有给78级正式开过课。听说陆先生现在还给本科生上课,这是非常感人的。
当时复旦还有不少好老师,圣约翰大学毕业的居多,譬如曹又霖先生。他从来不写(而且可能也不会写)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论文。曹老师对英语文本有着非常细腻的体会,他在精读课上带我们读小说,读作品,一点点读,同时不断地问“为什么”,让我们意识到文字背后复杂的人情世故和背景知识。
那时还有来自英国、美国的老师,他们授课任务重,与学生的交往多,经常借书给我们看。老一辈的学者有伍蠡甫、葛传槼、杨岂深等,他们都带研究生,随时可以请教。有一位教过我们的老先生叫潘世兹,原是圣约翰大学教授。他家在长乐路有一栋大房子,叫“宝礼堂”,是有名的藏书楼。他父亲藏有一百多部宋元版本的古籍,抗战时这些国宝级的文物由英国军舰运到香港汇丰银行保存,解放后潘世兹先生把所有这些图书(还有很多瓷器)捐给北京的国家图书馆。潘先生是外文系的英语教授,兼复旦图书馆馆长,他真是一位非常可爱的人物。教过我们的还有索天章、孙骊和夫人巫漪云教授。
我现在还与丁兆敏老师有联系,她待学生非常热情。我那套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57年作家出版社出版)还是丁老师前年送给我的。我在七十年代初自学英文,用的是徐燕谋先生主编的大学英语第七、八册,实际上是贪心,根本没学好。进复旦后,徐燕谋先生还健在,但是身体不好,不参加系里的学术活动,我从未见过。徐燕谋先生中文根底厚实,是钱锺书先生的诗友。陆谷孙先生是徐先生的高足,在中文的造诣上是有传承的。
南都:你作为一个成长于毛泽东时代从社会主义国家出去的年轻人,1983年去英国剑桥大学留学的经历中有没有让你感触特别深的记忆?
陆建德:你说的“社会主义”并没有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有时候就是名义而已,不是很重要。留学生到了英国以后,大家看到一些很不能理解的事情,比如英国学生经常组织慈善活动。我所在的达尔文学院有位叫Wendy的女生报名参加伦敦马拉松赛,目的是要为非洲某一个地方的医务室募集资金买一台心电图机,她去比赛,只求跑完全程,名次无所谓。出发前她在学院的信息板上贴出一张大纸条,希望大家热心支持,写下名字和捐助的金额。但是中国学生对这些慈善活动不大感兴趣,很少参与。你觉得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学生的特点吗?也许我们以为自己国家的政府在做这些事情,个人没有什么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