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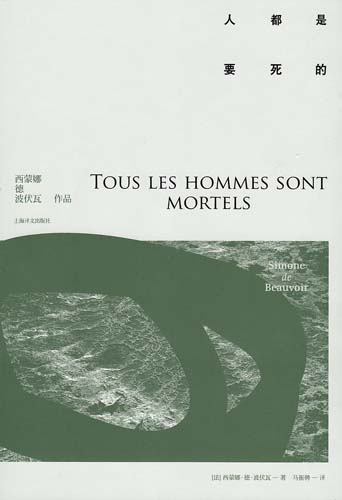 人都是要死的,波伏瓦选择了一句废话作为她这部小说的标题,当然,这也是一句真理。这句话挟带着一股来历不明的力量,最和它相匹配的回音,应该是一阵振聋发聩的沉默。说它的人,肯定不仅仅为了说出它,更像是在请求我们安静,好说出更多的话来。我突然记起,司马迁也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人都是要死的,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由此,我想到的是,前半句作为毫无价值而又不容忽视的真理,往往以被悬空的声音的面貌出现,尽管已是一个结论,但关于这一命题的思考才刚刚开始,显然更重要的结论还掩藏在随之而来的短暂沉默中。 人都是要死的,波伏瓦选择了一句废话作为她这部小说的标题,当然,这也是一句真理。这句话挟带着一股来历不明的力量,最和它相匹配的回音,应该是一阵振聋发聩的沉默。说它的人,肯定不仅仅为了说出它,更像是在请求我们安静,好说出更多的话来。我突然记起,司马迁也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人都是要死的,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由此,我想到的是,前半句作为毫无价值而又不容忽视的真理,往往以被悬空的声音的面貌出现,尽管已是一个结论,但关于这一命题的思考才刚刚开始,显然更重要的结论还掩藏在随之而来的短暂沉默中。
书写一个永远不死的人
这看起来似乎很冒险仅依据一句话里的字面元素,进行一次不甚严谨的反向推导,匆匆得出这个摇晃在虚拟语气上的论断。然而,它却正好与小说主人公福斯卡的生命处境带给我们的感受相契合。600多年的历史在这位亲历者身上结出的果实,既不是重,也不是轻,而是虚无,越来越多的虚无。这是一个永远不会死的人,既不会死于时间的流逝,也不会死于任何蓄谋或突发的事件,甚至连自己也伤害不了自己。也就是说,他无法做到在一个他认为适当的时机,对时间喊出那声“停”。当他的生命还能像泰山一样沉重时,他未能就此死掉、去获取这沉重;当他的生命变得像鸿毛那样轻时,他也无法就此死掉,以挽留这最后的重量。
我想起左拉写过的一个短篇《人是怎样死的》。小说分为五个部分,讲述了五个人物的死亡,以及亲人们对他们的死作出的各种反应,每部分都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故事。我其实很希望能找到证据,证明波伏瓦的这个标题来自左拉,但我所有的发现只不过是,她的这部小说也同样分为五个部分,分别对应福斯卡在回忆自己的经历时讲述的五个不同时期的故事。
五个时期分别是:13世纪末至14世纪中叶四分五裂的意大利,16世纪的日耳曼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王国及其殖民地南美,17世纪的北美,18世纪的法国启蒙时代,以及爆发了1830年革命和席卷欧洲的1848年革命的19世纪的法国。直至他回忆这些往事时,他已存活了6个多世纪,还将一直活下去。在一部声称“人都是要死的”的小说里,波伏瓦讲述了一个绝对的特例,一个不死的人。
他羡慕所有能死去的人
福斯卡永远年轻。这意味着他会不停地经历爱情和欲望,而压制欲望又将成为他所有欲望中的一部分。但不管是爱情,还是欲望,都变得没什么意思,在那么多的、一个比一个更遥远的未来里,找不到这些正在经历着的美好或邪恶的事物的投影,那里留给他的是无穷无尽的未知和遗忘。他见证了一代又一代儿子的死亡,女儿们像花一样凋谢,而他还是那么年轻,吸引着那些比他外孙女还要年轻几十岁或几个世纪的女人。他羡慕所有的人,因为他们可以在某一天死去,而他却无法做到这一点。
这是一个不可逆的选择,他没有任何机会可以推翻当初的决定。在32岁那年,正统治着意大利一座小城卡莫纳,并与热那亚人进行着艰难斗争的他,喝下了一个乞丐献给他的神秘药水。他那时渴望不死,希望有足够的时间去征服世界。三个世纪后,他曾自杀过,用枪朝着胸口和嘴里各开了一枪,但只是晕眩了一会儿。在小说刚开始不久,为了向读者证实自己的处境,他用刀片割开了咽喉,伴随着一股冒出来的鲜血,他倒在地上看上去已经没有了呼吸,但几秒钟后他又睁开眼睛平静地说话了。在整部小说里面,这是非常奇怪的一幕:它显得如此突然和仓促,使本该是纯粹的思想游戏滑向了现实,一个冥思行为被动地陷入全面的真实性和严谨性的纠缠和质疑中。
献给让·保罗·萨特
波伏瓦将这部小说献给一个人献给了让·保罗·萨特。而对这部小说里那个死来死去都死不掉的主人公,最可能产生质疑的人是谁?我想,正是萨特的小说《恶心》里的主人公罗康坦!罗康坦深刻的悲观和怀疑不仅是感受性的,而且也是思辨性的,他的思维严谨、富有某种形而下的尖锐,并善于发掘各种狭窄的可能性,他不仅会热烈地赞同福斯卡去死,还将为他冥想出至少五种不同的死法。
死法一(比方说),让人一刻不停地杀他,直到永远。喝了不死药水之后的福斯卡只是获得了恒久的生命,但是他的肉体仍然是可以伤害的。小说里面也写到,在受到致命伤害后,他将短暂地“死去”。如果将这些短暂的死亡状态持续施加在他身上,便达到了令其长眠的目的。“我要是福斯卡的政敌,”罗康坦也许会这样想,“我要下令我的子子孙孙,每分钟杀他一次。”
死法二,将他的肉体绞碎,残骸撒遍世界各地。如果说致命的伤口能自动愈合,尚不至于破坏掉思考生死问题时所必需的严肃氛围和某种前提性,那么当你不得不先想象一番,无数块碎肉从各大洲漂洋过海、缤纷而至,并重新拼凑出人形,才能继续思考“生存,还是死亡”。那简直像是在开玩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