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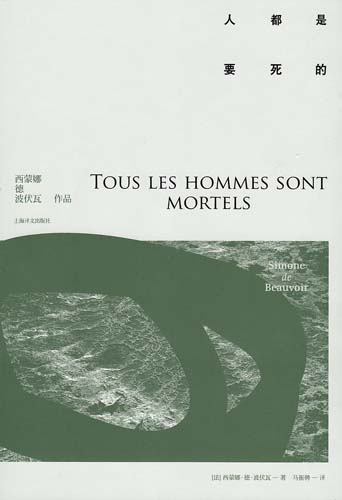 提起西蒙娜·波伏娃,我的脑海中情不自禁地浮现出近二十年前初读其回忆录时的情形:那是一册名为《西蒙·波娃回忆录(第一卷)》的平装本,比后来我在图书馆见到的煌煌八大卷的精装本,显然要简陋得多。事实上,当我在离家仅几步之遥的小书店见到它时,并不知道作者究竟何许人也。我记得自己站着翻看了一会儿,被其中的异国情调和青春叛逆氛围吸引,很快就决定将其收入囊中。直到今天,我都认为,这是我阅读生涯中一个难以忘怀的时刻,足可以用“酣畅淋漓”来形容当时的感受。之后,我便一发不可收地阅读了作者和萨特的许多作品:《第二性》、《名士风流》、《女宾》、《人都是要死的》……以及萨特的自传、随笔,直至有一天,我对自己发誓,要将《存在与虚无》这样晦涩的哲学著作啃下来——幸好后来没有实行。说来好笑,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认真地以“存在主义者”自居。但我相信,彼时的阅读体验是真实的,它带给我的某些东西早已深深地植入了我的灵魂,也许一辈子都根除不了。 提起西蒙娜·波伏娃,我的脑海中情不自禁地浮现出近二十年前初读其回忆录时的情形:那是一册名为《西蒙·波娃回忆录(第一卷)》的平装本,比后来我在图书馆见到的煌煌八大卷的精装本,显然要简陋得多。事实上,当我在离家仅几步之遥的小书店见到它时,并不知道作者究竟何许人也。我记得自己站着翻看了一会儿,被其中的异国情调和青春叛逆氛围吸引,很快就决定将其收入囊中。直到今天,我都认为,这是我阅读生涯中一个难以忘怀的时刻,足可以用“酣畅淋漓”来形容当时的感受。之后,我便一发不可收地阅读了作者和萨特的许多作品:《第二性》、《名士风流》、《女宾》、《人都是要死的》……以及萨特的自传、随笔,直至有一天,我对自己发誓,要将《存在与虚无》这样晦涩的哲学著作啃下来——幸好后来没有实行。说来好笑,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认真地以“存在主义者”自居。但我相信,彼时的阅读体验是真实的,它带给我的某些东西早已深深地植入了我的灵魂,也许一辈子都根除不了。
例如这册近日由上海译文出版社重版的《名士风流》。当年首度读它时,我大概还是第一次接触许钧的译笔——真是地道得很,有法国味而又不失母语的尊严。全书开篇便将我们带入了战后法国知识分子精英圈那种追求与幻灭、希望与失望、沉沦与奋起并存不悖的氛围中,每一个角色,从“男一号”、身为法国知识界左翼领袖人物的亨利(原型乃萨特无疑),到“女一号”、知名精神分析学家、同属左翼阵营的安娜,从亨利的前情人、有“最美的女人”之称的波尔、“新女性”纳迪娜,再到投向右翼的朗贝尔,每一个形象都丰满而令人信服。亨利和罗贝尔这两位老友,因 “苏联劳改营事件”出现分歧。亨利因坚持客观报道的原则而被认为是帮助了苏联的敌人,最终被左翼知识分子排除在外。罗贝尔虽然支持苏联,但确信自己必然不能适应共产主义那种严整、刻板的生活,导致他所领导的左派运动最终解体。罗贝尔由此感叹道,“我们想独立于两个阵营之外,其实却无能为力。”在小说结尾,两位老友言归于好,但保持了各自的信念。稍知战后法国知识界状况的读者读到此处便都能心领神会:小说在这里影射的是萨特与加缪这对老友,只不过小说虚构了一个比现实更为“光明的结尾”。《名士风流》出版后好评如潮,获得1954年度龚古尔奖,波伏娃终于得以“作家”而非“萨特情人”的身份在战后的法国乃至欧洲文坛占据一席之地。
如果说,这部小说是对作者身处的知识精英圈的“高保真”临摹,那么在《人都是要死的》一书中,波伏娃则发挥了其与生俱来的文学想象力,纵横千里,跨越四海,书中主角、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帝王谋士雷蒙·福斯卡带着对生命和世界的困惑而选择远离政治,去到加拿大勘探广袤的疆域,其后又奇幻般地亲历了法国大革命、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等重要历史时刻,在此过程中,不仅见识了世界的繁复,更悟到了人之为人的存在价值。在这部小说中,波伏娃这位法国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中学教师资格考试通过者——这项考试素以严格著称,伟大者如萨特当年都曾在此项考试中受挫,而波伏娃通过考试时年仅21岁——充分展现了其严密的理性思考能力和丰盈的艺术表达力,令读者不得不感叹这位女性作家的天分之高。
波伏娃的小说,总体上遵循了传统的模式,在这一点上,她似乎无意玩弄技巧,但这绝不意味着她的小说没有技巧可言。固然,在一些当代读者看来,波伏娃的小说有点“过气”,其中所描写的意识形态纷争于今看来都已烟消云散,似乎不值一提,其实不然。原因在于,波伏娃的小说以及像《第二性》这样的作品,在当年之所以能够风靡一时,令上世纪80年代初识“自由”滋味的中国年轻人为之着迷,除了“潮流”这一不可忽视的因素外,作品中提出的诸如“人的存在与自由选择的关系”这样根本性的哲学命题,以及当年曾经弥漫法国知识界、欧洲知识界乃至全世界的意识形态之争,于今看来仍然有着不言而喻的现实意义,这也正是其作品生命力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位堪称“经典”的作家与普通作家的主要区别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