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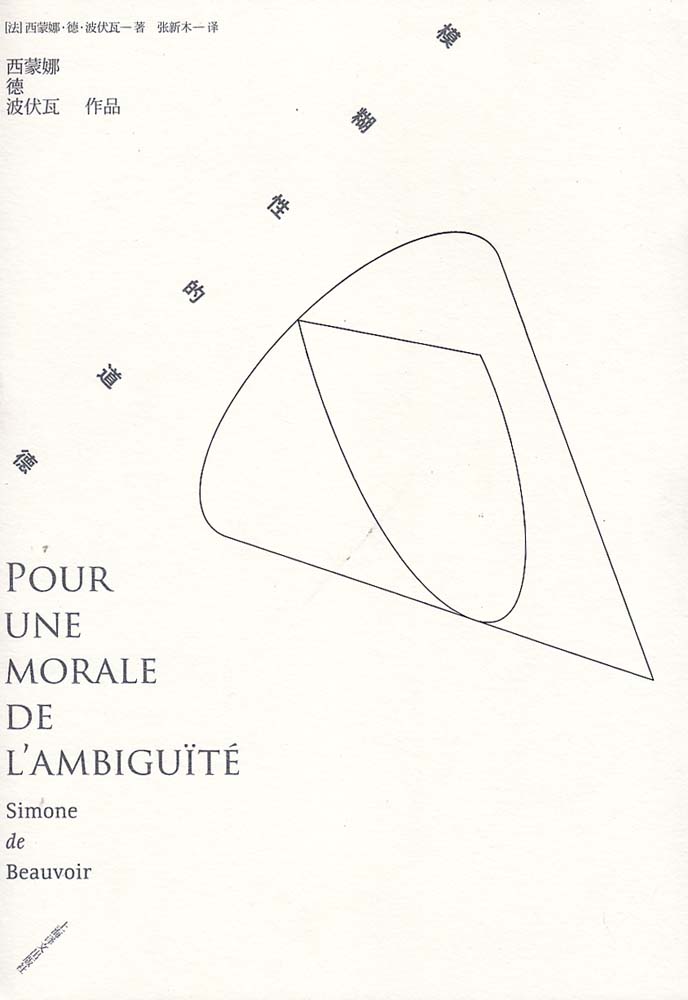 萨特在《存在与虚无》里说:“人是一堆无用的激情。”三十年前很多人初读萨特,被这句话打动得肝摇胆晃,三十年后仍旧心有戚戚,只是过去的情绪更多地为集体命运所喷发,现在则出于顾影自怜。欧洲哲学到了萨特手里,已经认不出它自己了,伏尔泰雄辩,黑格尔冷峻,马克思豪迈,光辉万丈的启蒙主义在两次大战前后彻底沦陷,主要代替品之一是承认无能、揭露荒谬的存在主义。存在主义经常讨论自由,讨论责任,但是萨特自己的戏剧《死无葬身之地》,他的小说《墙》,都是设计一个有限制的环境,拷问在其中的人的选择困境——他们的自由很有限,而做出的每一个选择又都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别人的自由,同样,自己的命运也会被别人的一个偶然的自由选择所决定。 萨特在《存在与虚无》里说:“人是一堆无用的激情。”三十年前很多人初读萨特,被这句话打动得肝摇胆晃,三十年后仍旧心有戚戚,只是过去的情绪更多地为集体命运所喷发,现在则出于顾影自怜。欧洲哲学到了萨特手里,已经认不出它自己了,伏尔泰雄辩,黑格尔冷峻,马克思豪迈,光辉万丈的启蒙主义在两次大战前后彻底沦陷,主要代替品之一是承认无能、揭露荒谬的存在主义。存在主义经常讨论自由,讨论责任,但是萨特自己的戏剧《死无葬身之地》,他的小说《墙》,都是设计一个有限制的环境,拷问在其中的人的选择困境——他们的自由很有限,而做出的每一个选择又都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别人的自由,同样,自己的命运也会被别人的一个偶然的自由选择所决定。
萨特将自己的戏剧称为“处境剧”,认为他所刻画的是最真实的处境,因此讨论的也是最贴近现实的问题。至今我们还能感觉到这些作品的力量,我们还会在两难之间挣扎:在处处受制的环境里,在工业社会安排好的职业角色之中,在各种伦理责任的牵绊之下,我们作为人,如何来满足追求无限的先天欲望,或者说浅一点,如何实现“自我价值”?萨特的存在主义作了回答,而这种回答的动人之处,就落在萨特的“自由情侣”西蒙娜·德·波伏瓦的一句话里:存在主义不以任何抽象的逃避来慰藉读者;存在主义不主张任何逃避。
既然不逃避,那么就得直面困境,有所担当。在西蒙娜·德·波伏瓦思考和创作的盛年,世界格局从二战进入冷战,民权意识苏醒,斜阳中的帝国还得面对日益尖锐的殖民地问题,“压迫”、“奴役”这些主题成为左派学者们关心的重心所在。黑格尔、马克思都分析过奴隶的处境,鲁迅的“奴隶论”和“铁屋子”比喻,都讨论了“奴隶需不需要自由”这一问题。波伏瓦在《模糊性的道德》中也说到:在美国,卡罗莱纳州,蓄奴制度的拥护者对北方胜利者说,那些年老的黑奴在自由面前晕头转向,不知道这自由有什么用,“哭着喊着要回到他们从前的奴隶主身边;这种虚假的解放……困扰着那些曾经是牺牲品的人,像是盲目命运对他们的新打击”。波伏瓦说,消除奴隶的无知状态是解决这一困境的唯一办法;而同时,“自由是人类普遍的事业”,我要想让奴隶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我就要不能让自己成为暴君——包括不以逃避的方式成为暴君的同谋。
奴隶是个极端的状况,现实中的人们既有知,又有比奴隶更多的自由。但是,从“奴隶的自由要靠其他人不做暴君”可以引申出两个观察:第一,压迫性的人际关系有时是通过无知来确立的,有时则仅仅是靠着暴力统治;第二,人的行动之间是彼此关联的,任何人都无法单枪匹马地拯救自己的自由。在“行动的二律背反”一节中,波伏瓦继续从一个特别的角度检视人类行动:任何一个行动都不孤立,而是会与不同人群产生关联和影响,“压迫者在善意的人们眼中体现为人为性的荒诞……道德要求自由战胜人为性的胜利时,也要求人们消灭压迫者……在这里,必须把他人当作一个物体,对它施行暴力,用这种方式来确认人类分裂的痛苦事实……”这些论述表明,波伏瓦不是要简单地鼓励为奴隶解脱无知和受压迫的束缚,并以此为满足,她希望超越压迫—被压迫的死循环:谁都不想被当作物来看待,但是,为了不被当作物,就势必要把他人物化,牺牲他人。
怎么超越呢?说穿了也简单,首先要看透道德的“模糊性”。波伏瓦并不简单地对蓄奴者、对资本家、对第三帝国、对苏联作道德批判——这些人或政权的共同点都是设法把人物化,为自己所用,多数政治家都会很迅速地把理念抬高到内容以上的位置,用牺牲无辜者的生命以推进实现自己想要的目标。但是,即使我们只是一个下等士兵,一介小职员,或一个普通的父亲,也都会遇到非如此做不可的情况;我们每天都需要在同等分量的价值之间抉择,不是损伤别人,就是损害自己。用哲学话语说,现代人,一旦他意识到他的存在的本质是主观的,自己的人生不可能建立在任何绝对客观的理念之上的话,他就会发现自己坠入道德的模糊性之中。
存在主义的一个基本讨论框架,是研究处在超越性和物化性之间的人的自由问题——不那么抽象地说,就是人不是想接近纯主观的神,就是想靠拢纯客观的物。对波伏瓦来说,严峻的现实是,压迫者决定着被压迫者的自由,迫使他们徒劳地在超越性欲望中挣扎,实际上则被物化:切断被压迫者与未来的联系——就好比自己成了一部分先发达起来的富人之后,就开始拟画把其他人限制在温饱范围之内,并为自己获得的优待而感恩。她一面要揭露和反对这一压迫性的事实,另一面,她试图用“人在根本上都是自由的”这一存在主义核心信条来启发普通人,让他们都意识到,不管是追求绝对的主观还是绝对的客观,都是在自我欺骗。所谓的“模糊性”,按我的理解,指的是生命并不是包一个结结实实的意义包裹交到你的手里——你必须先了解所有不美好的现实,在此前提下随时创造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