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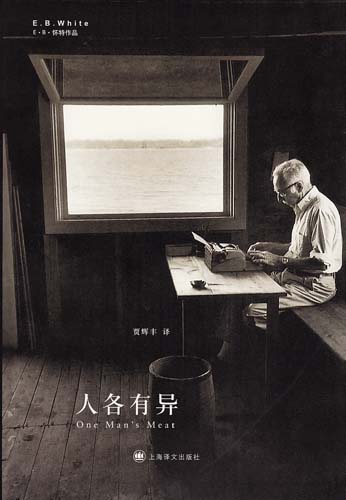 不知中国古代的诗人陶渊明归园田居,除采菊东篱、悠见南山之外,维持生计必需的农活是否亲力亲为?大概作为离职的官员,还是有经济余裕请得起家仆的,自己需要做的或许并不多,否则未必会有悠然之慨了。而美国作家E.B.怀特在一九三〇年代末自纽约搬至缅因州咸水农场,其田居生活很有货真价实的“料”,如某一年生产指标是四千打鸡蛋、十头猪,九千磅牛奶,他还要给农场里的十几只母羊接生。散文集《人各有异》,即为怀特五年田居生活的点点滴滴的记录,其对简朴生活的所思所想充满了多种可能性,摈弃“我们”,反求诸己。 不知中国古代的诗人陶渊明归园田居,除采菊东篱、悠见南山之外,维持生计必需的农活是否亲力亲为?大概作为离职的官员,还是有经济余裕请得起家仆的,自己需要做的或许并不多,否则未必会有悠然之慨了。而美国作家E.B.怀特在一九三〇年代末自纽约搬至缅因州咸水农场,其田居生活很有货真价实的“料”,如某一年生产指标是四千打鸡蛋、十头猪,九千磅牛奶,他还要给农场里的十几只母羊接生。散文集《人各有异》,即为怀特五年田居生活的点点滴滴的记录,其对简朴生活的所思所想充满了多种可能性,摈弃“我们”,反求诸己。
怀特说自己决定把家连根拔起、从城市搬到乡村,一是在《纽约客》“不能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来写作”,再有居于纽约租住的房子里,从来没有家的感觉,于是“就像个疯癫的流浪风笛手一样,率领我的小家离开了城市”。其实,怀特这看似突兀的举动与他所崇敬的思想者梭罗是分不开的,梭罗隐居瓦尔登湖畔的生活方式与著述想来深深影响了怀特,因之业已年近四十岁,怀特仍旧接受独立思想与独立生活的召唤,毅然前往留有其童年印记的缅因州乡村生活,真切地操持一个农场的事务,这时的写作,大约应放在其农夫的工作之后了。
怀特对农事有浓厚的兴趣,他不仅不辞劳累地去做,而且兴致盎然记录下来,且有深切的思考。怀特有着做农人的勤劳,也具真心的喜爱。这是一位优秀的文体作家,其敏锐的观察力和洞察力可以将这一切细微的物什记录下来,见证简朴生活的清澈与可能性。
在缅因州农场,于怀特而言,最大的收获莫过于找到了“我”,以此作为发言的立足点。这事出有因,先前在《纽约客》,作为评论员的怀特,“社评用语‘我们’让我困惑,这是个模糊字眼儿,意味集体的深刻或机构的共识。我想写得尽可能明白,没有丝毫含糊。”怀特没有明言的是,集体的模糊性也往往倾向于对个体自由的威胁与妨害,在某些特定条件下,以堂皇的名义为掩护,“个”在“群”的覆盖下可能会遭受灭顶之灾。而归园田居之后,怀特不管是谈农场、自耕农、牧人生涯、野营布道会、镇民会议、缅湖,还是谈夏季鼻炎、儿童读物、波士顿猄犬、羊群、堆肥、猎熊、歌鸟、奶牛、汽车、欢乐牌冰淇林,都自始至终贯穿着“我”的声音,将自己的存在感发挥到了极至。在某种程度上,不论怀特谈什么,事实上都在谈他自己,因为万物入“我”眼,皆著我之色。
不必再替“集体”代言,想必让怀特松了一口气,体会到简朴生活的美妙。他于农务中体尝到了乐趣,也于对其的书写中感觉到立足于“我”的酣畅与明晰。而有意味的是,在如此务实而单纯的生活中,怀特的独立思考非但没有消泯,反而更其活跃起来,他可以自时政大事谈论话题,也可以由生活中的针头线脑引出。如一天,收到了政府配给的石灰石粉,引起了怀特的细细思索与用心鉴别,“我确实感觉到,本届政府热切地想要对我和我的土地实施善意的控制,‘调整’我,同时改变我的高地田的土壤反应。”见微知著,怀特时时没有忘记对“集体”的警惕,这根弦表面似乎绷得有些紧,但自公民的角度看,怎样的警觉都是不过分的。
怀特之追求简朴生活,在他的时代,不知有没有受“不识时务”之讥;而若放在当下这个喧嚣的掘金年代,的确是个另类举动(自然亦有人付诸实践)。怀特认可的生活方式显然与物质无关,而是审美的,但如此精神层面的追求并未使怀特凌空蹈虚、不着实际,他踏足于泥泞与尘埃中,真真切切地做着一个农夫份内的所有实务,“谷仓里神秘地出现一捆干草,又冒出一只矮脚鸡,自得其乐地生活”,此种场景不论于他的想象抑或现实中,均为切实映像。固然,五年之后怀特结束了他的农场生活,又回到了城市,但如其所说,人的一生总会有些时候,头脑异常清醒,而不是迷迷糊糊,这几年就是如此的状态。人总有思想的困惑与扰乱,也面临着诸多的选择,此时是遵从内心的召唤,还是屈服于外在的压力,是个体独立与否的问题,怀特选择的是“立即动身,从哪儿来,回哪儿去”,那我们自己又该如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