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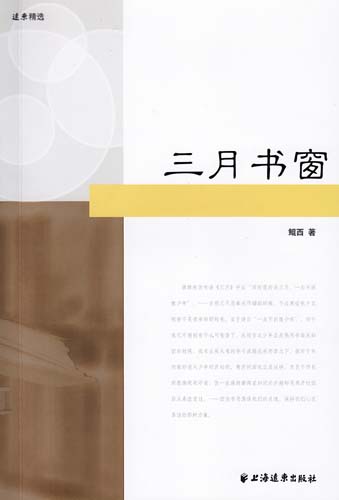 坊间流行各类随笔,成为一种“景观”。重读鲲西先生的《三月书窗》,书里那些清澈的思想,娓娓的笔致,使人忘倦,也让人怀想世纪老人的意绪风流。 坊间流行各类随笔,成为一种“景观”。重读鲲西先生的《三月书窗》,书里那些清澈的思想,娓娓的笔致,使人忘倦,也让人怀想世纪老人的意绪风流。
鲲西先生本名王勉,为上海古籍出版社退休编审,现已尊享九十六岁高寿。书名取自唐韩致尧诗《三月》:“四时最好是三月,一去不回惟少年。”于四时三月,书窗内闲话,诚然是一种雅致的生活,然而,对书有如此热忱,在鲲西先生也不免极具个人色彩。虽在古籍领域孜孜矻矻编书,但鲲西先生谈莎士比亚、歌德、纪德、吉本、叶芝,却随手拈来,对西学的涵泳经营,可以与研究者相媲美。钱伯城先生是他订交四十载的老友,相知甚深,为此书作序时,情不自禁赞誉道,鲲西先生是“博览群书,中外兼擅,尤邃于西学”。即从《三月书窗》也可得知,此书不属于端然厚著,只是一则小书,全部加起来,不过三十余篇,十多万字,语言也并不古奥难解,恰似一种自由适宜的风格,却给予人如管弦般的鸣奏感。
收入书中的文章,大都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鲲西先生的兴趣范围颇广,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绘画、音乐,次第写来,毫不费力;既关注大家学者陈寅恪、钱锺书、王国维、罗素、霭理士、维特根斯坦等,又回忆清华师哲潘光旦、吴宓,即使写闽籍乡贤,也周旋于遗老胜流之间,如同光诗派、黄秋岳等,并穿插有文史考证,落笔掷地有声,行文自然显得厚重。他的阅读视角如此宽域,其中缘源有自,在他从学时,因战争北方三校的文法学院迁至云南蒙自,这一段时间,他既听陈通夫先生讲斯宾塞和人口问题,又去听钱宾四先生的中国史,还对叶公超先生讲解的十八世纪英国感兴趣……这段的独特受教经历,自然赋予鲲西先生不同寻常的含英咀华能力。
鲲西先生曾写过有关《红楼梦》、《金瓶梅》以及袁中郎、吴梅村、汪中等论文,但作家本人并不为之深喜。反而,他敝帚自珍这些深邃的随笔小文,并将平日里的阅读随感,以平和朴淡的心态安置在文字脉络中,赋予爽朗中肯的品评。因而,尽管不同质,在他的笔下,钱锺书与福斯特、《维多利亚女皇传》与《柳如是别传》、奥斯丁与《长恨歌》,遂得从容地被并置,这种中西混杂的阅读视角的取径,条清理晰地显现在各篇文章中。我读后,尤其对《弦外之音》、《音乐·绘画·小说》这样的篇什之文印象颇深。前者是谈对维特根斯坦的片读式读书笔记的一些感悟,他对《文化和价值》一书的那些评述,呈现出平时阅读思考的深度,令人深感兴趣,也引起对音乐经验的一些回味;后文则借助自己的才识,概述了音乐、绘画、小说的关系,从托尔斯泰探讨文学和艺术的《什么是艺术》这本书谈起,由此将纳博科夫、赫胥黎、托马斯·曼、里敦·斯特莱切、普鲁斯特、奥斯丁、詹姆士等人对艺术的态度、感观,以一种全息式的场景展现出来,这是一种独特的才情演绎。作者由此及彼的联想,是为求文评简约的必然手法,评述之外,又有流水的随感性质,体现出他为文和煦温厚的一面。
写文史随笔不易,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许多作者才华虽好,识见若是平常,使人不免明于此而昧于彼。鲲西先生却能以异常敏锐的感知,慧眼谈出些不同,识见尤为可嘉。他是属于那种平和温淡的老派文人,从驳杂琐屑的谈论可知,他坐拥书窗,读书勤勉无已,以至于他的欣赏趣味相当宽松,有一种大而化之的平和淡朴气息。
翻开书扉,记有他的一段话:“人必须对于他自身以外的事物怀有兴趣,然后才能使他对人类的普遍价值看得特别重要。”在阅读日趋分化的人文环境里,读文史随笔总有将人凝聚在一起的力量。如此循旧守雅的读书修养自觉,需得从温厚端润的老一辈学人那里获得。寒夜冬夕,于书窗之外,听鲲西先生的文史闲话,绮怀旧梦,颇增烟云之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