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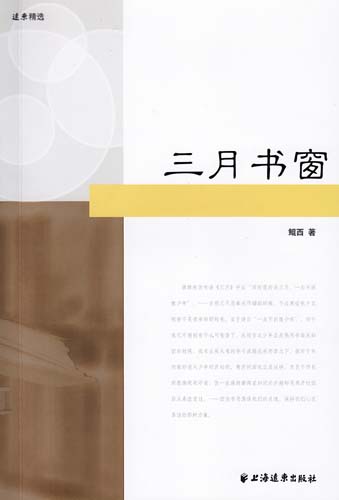 唐韩致尧有诗《三月》中云“四时最好是三月,一去不回惟少年”,前读陈寅恪先生诗及文,尝取韩集读过,而竟没有看到这样好的一联,后来尚是翻钱默存先生著《谈艺录》补遗中始见此句,深喜之。因取“三月”意名这本小集。自然三月是春光明媚的时候,不过寒夜秋夕又何尝不是读书的好时光。四十年代中长住昆明,那里最是一年到头都是和煦的季候,差不多做完一天工作之后,我总是在灯下展读莎士比亚一二小时,一天的疲惫全都消失了,但觉得胸中既激荡又平静,这是莎士比亚所赐与的,没有什么更能形容这一种读书所得的快乐了。至于诗云“一去不回惟少年”,对于我已感不到有什么可怅惜了,反而言之少年正是热爱书渴求知识的时候,我自认我从来的学习成绩总在侪辈之下,但对于书的爱却是从少年时开始的。离开校园也正是这样,有负于师长的教诲使我不安,但一生保持着探求知识的兴趣却是离开校园后从未改变过。前些天偶看到有一小文记一位学人下放于菜圃劳动,一时间误传将得到上调,后又成泡影,当其家人说何不即终老于此,答“没有书!”噫,书之用竟如是之大,只是因为它是荡涤我们的灵魂,保持我们心灵圣洁的那种力量。我所以有取于韩偓的诗,也有一点怀乡的心,因为韩后来避祸入闽,但其晚年如何正史本传都没有交代,我读王夫之《读通鉴论》觉得他对韩之出处评论极为公允,因之我对他入闽后究竟如何结局,怀着很大的好奇心,韩的身世,韩的时代是极富有历史涵义,好奇心或由此而来,若有机会当取吴挚甫评注本《韩翰林集》一读之,这是寅恪先生尝加以批注的。以上皆属题外话。 唐韩致尧有诗《三月》中云“四时最好是三月,一去不回惟少年”,前读陈寅恪先生诗及文,尝取韩集读过,而竟没有看到这样好的一联,后来尚是翻钱默存先生著《谈艺录》补遗中始见此句,深喜之。因取“三月”意名这本小集。自然三月是春光明媚的时候,不过寒夜秋夕又何尝不是读书的好时光。四十年代中长住昆明,那里最是一年到头都是和煦的季候,差不多做完一天工作之后,我总是在灯下展读莎士比亚一二小时,一天的疲惫全都消失了,但觉得胸中既激荡又平静,这是莎士比亚所赐与的,没有什么更能形容这一种读书所得的快乐了。至于诗云“一去不回惟少年”,对于我已感不到有什么可怅惜了,反而言之少年正是热爱书渴求知识的时候,我自认我从来的学习成绩总在侪辈之下,但对于书的爱却是从少年时开始的。离开校园也正是这样,有负于师长的教诲使我不安,但一生保持着探求知识的兴趣却是离开校园后从未改变过。前些天偶看到有一小文记一位学人下放于菜圃劳动,一时间误传将得到上调,后又成泡影,当其家人说何不即终老于此,答“没有书!”噫,书之用竟如是之大,只是因为它是荡涤我们的灵魂,保持我们心灵圣洁的那种力量。我所以有取于韩偓的诗,也有一点怀乡的心,因为韩后来避祸入闽,但其晚年如何正史本传都没有交代,我读王夫之《读通鉴论》觉得他对韩之出处评论极为公允,因之我对他入闽后究竟如何结局,怀着很大的好奇心,韩的身世,韩的时代是极富有历史涵义,好奇心或由此而来,若有机会当取吴挚甫评注本《韩翰林集》一读之,这是寅恪先生尝加以批注的。以上皆属题外话。
收入本集的约三十余篇小文大都写于八十年代以后,在过去十余年里也以一部分时间写过一些论著,但敝帚自珍,我却喜这本集中的短文,因为它或许更代表真实的我。论文或不免矜持,以至时有仓父气,我写过有关《红楼梦》、《金瓶梅》以及袁中郎、吴梅村、汪中等论文,虽不无个人见解,但终觉不纯,这就是论文难写之处。集内文大约分书评和回忆两类。书评是一门艺术,它要言之有物,文不宜长,它又必须具有作者个人的风格。四十年代我最欣赏叶公超先生写的叶芝编《牛津现代英诗选》一篇长评,发表于《文学杂志》,谈英诗如数家珍,叶集已出,读者不妨取一读,定信所言不虚。
书和其他艺术如音乐、绘画都靠朋友之间相互传递信息,我把这叫做种子,我之得读亨利·詹姆士和E.M.福斯特小说皆出于卞之琳的推荐和介绍,所以别人影响我的,我也会影响别人,这就是如下种子一样的作用。周学普译《歌德对话录》就是徐君高阮临歧执手告别之际介绍我读的,是我最爱读的书之一,徐君墓木已拱,此际又想起“一去不回惟少年”这句诗,只是更为悲怆罢了。
此书承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先生热心肠而收入“火凤凰文库”中,除了感谢之外,使我欣喜的是于暮年又结识了一位爱书的朋友,人生何处不相逢,然而相逢又岂是容易,此所以于欣喜中又不免于怅怅。老友伯城允为本集作序,伯城亦知我者,序有过誉,甚感惶恐,并在此志谢。是为记。
鲲西
一九九六年十月廿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