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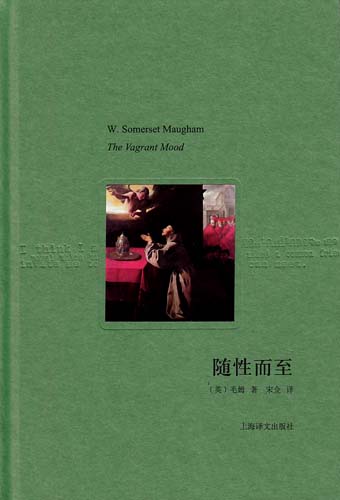 威廉·萨默赛特·毛姆早年经历坎坷,不到十岁父母就相继去世,他被送由伯父抚养,进入坎特伯雷皇家公学后,他又因为口吃和身材的关系备受羞辱。这让他对于人性的复杂和多变始终保持着敏感,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他的写作习惯。《随性而至》和《观点》两本文集分别出版于1952年和1959年,其中一些篇目是人物传记,另一些是文艺评论,但也写得像人物传记。 威廉·萨默赛特·毛姆早年经历坎坷,不到十岁父母就相继去世,他被送由伯父抚养,进入坎特伯雷皇家公学后,他又因为口吃和身材的关系备受羞辱。这让他对于人性的复杂和多变始终保持着敏感,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他的写作习惯。《随性而至》和《观点》两本文集分别出版于1952年和1959年,其中一些篇目是人物传记,另一些是文艺评论,但也写得像人物传记。
《诗人的三部小说》的开篇,毛姆说:“为什么时至今日,关于歌德的评论,该说的全都说尽,而我还要再写这篇文章来谈谈他的小说呢?其实,我不过是乐在其中罢了。”接下来他有些半推半就地表示:“我并不想赘述歌德的生平;不过既然他亲口说过他所写的每篇文字都或多或少是在讲自己,那么我也不得不提到他生命中的种种逸事。”
在《短篇小说》一文里写到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时,毛姆又故技重施:“我不想讲她的生平故事,但是因为她的小说大部分都有强烈的自传色彩,我还是简述一下吧。”
而在《三位日记体作家》中,他谈到保罗·莱奥托父亲的一段不伦恋情时,彬彬有礼地说:“接下来的事情我也不知道该如何文雅地表达……”当然接下来他的重点全在其上。
毛姆对作家的生平津津乐道,其中不乏如珠妙语,比如提到歌德抛弃初恋情人时就用“年轻的心灵总是坚韧刚毅,他人的苦难无法将其摧垮”来揶揄他的做作和无情。而书中遭到最刻薄对待的恐怕非亨利·詹姆斯莫属,毛姆取笑他曾写出一出荒唐的剧本被观众起哄,事后却将此归因于剧本“超出了伦敦庸俗大众的欣赏能力”,以至于“剧院经理们从此坚信小说家是写不出好剧本的”。他进而说:“(亨利·詹姆斯)把自己看得太重了。一个人如果不停告诉你自己是个绅士,那不免要令人侧目。我想亨利·詹姆斯如果不是如此频繁地坚称自己是个艺术家,那他也许会更讨人喜欢些。”
毛姆也为自己的尖刻作出解释:“我更喜欢去揣测他们心中的秘密。我的个性决定了我不愿不假思索地接受一个人的表象价值,而且我很少被折服,我没有崇敬别人的能力。我的性格更容易被人逗乐,而非敬重他人。”他这么说时,我想到一段非常贴切的描述:“虽然他作出这一评论时带着歉意,但很明显,他乐于说一件让人略感不悦的事情。”事实上,这段描述也是出自毛姆的手笔,当时他正游历中国,拜访辜鸿铭。临走时,辜鸿铭送他两首小诗,毛姆后来请他认识的一位汉学家作了翻译,译文如下:
你不爱我时:你的声音甜蜜;
你笑意盈盈;素手纤纤。
然而你爱我了:你的声音凄楚;
你眼泪汪汪;玉手让人痛惜。
悲哀啊悲哀,莫非爱情使你不再可爱。
我渴望岁月流逝,
那你就会失去,
明亮的双眸,桃色的肌肤,
还有那青春全部的残酷娇艳。
那时我依然爱你,
你才明了我的心意。
令人歆羡的年华转瞬即逝,
你已然失去,
明亮的双眸,桃色的肌肤,
还有那青春全部的迷人娇艳。
唉,我不爱你了,
也不再顾及你的心意。
诗歌令毛姆感到吃惊,因为当他说“更容易被人逗乐”时,逗乐他的也许正是诗歌所涉及的那种人性的矛盾反复。这符合毛姆对人的理解:“人从来就不是平板一块……人身上最为奇怪的是,最不一致、最不协调的品质往往集中于一个人身上,所以这人似乎就是一团矛盾,让人不明白这些品质到底如何共存,如何能融合在一起成为某种始终如一的个性。”
这种对立在埃德蒙德·伯克的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伯克是个道德家,改革家。他标榜自己的高风亮节,可居然运用权力把极不称职的人安插到利润丰厚的职位上;他标榜自己的诚实,可居然当众发表虚假声明,说自己从未涉足东印度公司股票。他始终与不公正和腐败作斗争,可自己居然不遗余力地帮助威廉和理查德的腐败欺诈行径。”可即使如此毛姆还是在某种程度上替他辩护:“有人说,他是个骗子,是个伪君子。但我不这么认为。有一种缺陷是大多数人所共有的……而这种缺陷在他身上被放大到了极端,那就是:什么符合他的利益,他就愿意相信什么。我不知道该把这种缺陷叫做什么,但他既不是虚伪也不是欺骗。”毛姆相信,当伯克回到他的书房,他又会是“那个思想高尚的人,那个以精神的高贵、人格的伟大与慷慨为朋友爱戴与尊敬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