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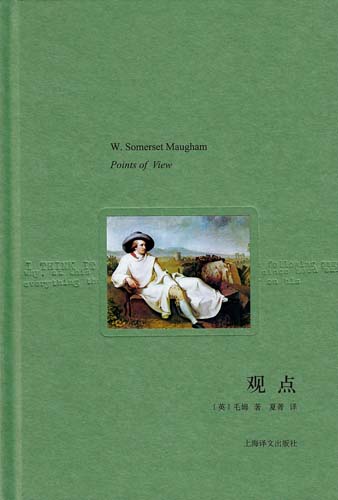 毛姆信奉“风格即人”,往好里说,这是面由心生推己及人,往坏里说,那就是以貌取人了。毛姆的以貌取人很是了得,他说亨利·詹姆斯小说中那些“繁复晦涩、冗长复杂和矫揉造作”之所以会为人接受,是因为詹姆斯在你印象里就是这样一个人,“魅力无穷、和善宽厚、自负炫耀却让人觉得有趣”——比之毛姆在《随性而至》中对詹姆斯的刻毒挖苦,《观点》中的这段评价还算厚道。 毛姆信奉“风格即人”,往好里说,这是面由心生推己及人,往坏里说,那就是以貌取人了。毛姆的以貌取人很是了得,他说亨利·詹姆斯小说中那些“繁复晦涩、冗长复杂和矫揉造作”之所以会为人接受,是因为詹姆斯在你印象里就是这样一个人,“魅力无穷、和善宽厚、自负炫耀却让人觉得有趣”——比之毛姆在《随性而至》中对詹姆斯的刻毒挖苦,《观点》中的这段评价还算厚道。
在《观点》中,毛姆也没少损人,比如他笔下的歌德就是一花心大萝卜,契诃夫博爱但“从未向谁敞开心扉”,等等。不过他倒未必纯然如龚古尔兄弟那样“勇于扯下‘伟人’的虚伪面具还原其真面目”,因为除《圣者》外,《观点》4 篇文章对一干文人虽然苛刻,但字字落到毛姆本人对小说艺术的洞察。同时他也提醒读者,“阅读一位小说家为他人的小说所撰写的评论时一定要有所提防,因为他所发现的优秀之处其实是一种自我认同,而对别人的作品里那些他自身所缺乏的特点却难以认可”。这段自白与毛姆对文人们的开涮一样顶真,他所提供的只是一个私人阅读经验,镜中观人,到头来看到的还是他自己。
问毛姆对哪些作家“难以认可”,不如问他对哪类作品不甚感冒。在《诗人的三部小说》中,毛姆对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评价甚好,他说此书矫揉造作,但它迎合了当时风起云涌的浪漫主义风潮,人们动辄“相思成灾,一病不起”并非全然虚构,而是生活实况。但到《亲和力》,歌德滥用“偶然性”的巧合因素来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无疑对作品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毛姆认为一部作品是否立得起来,首先在于情节是不是站得住脚,歌德“用化学物质作为人物原型”来写《亲和力》,只是使作品成了一个方程式怪胎,“演绎作者的抽象理论”,缺乏“生命力的鲜活气息”。
针砭背后,毛姆所推崇的无疑是自己的创作观,他在蒂乐生、莫泊桑和契诃夫三位作家身上找到了阐发自己“观点”的切入口(《短篇小说》)。他说莫泊桑的《项链》同样存在情节上的破绽,但没有读者想到要提出异议,这正说明莫泊桑的功力,“作家的职责并非只是忠实地记录生活,而是要将生活演绎成戏剧??他所面临的考验就是既能让读者觉得可信又能实现艺术效果”。而可信度这种东西也并非一成不变的原则,毛姆举出古希腊雕塑家并非按照现实主义进行创作的例子,来说明文学艺术对现实的扭曲并非20世纪独创,“人们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他们早已习惯于过去的艺术对现实的扭曲”。因而,作家的创作并非是要表达现实的真实,而是艺术的真实。“如果小说中人物的对话在我们看来太不真实,那必然是因为小说家觉得这样的对话才适合这个故事,能帮助他达到预期目标”。而“预期目标”是否真正达到,要看“你讲的故事”能否“让读者信服”。
类似观点我们也可以从弗吉尼亚·伍尔夫为现代小说所作的辩护《本涅特先生和布朗太太》中读到,有趣的是,对该小说理念的精辟阐述和实践使伍尔夫被奉为20世纪现代文学的经典作家,而毛姆却因不汲汲于文学革新中“对现实的扭曲”、只满足于在传统框架内锻造炉火纯青的写作技艺,而被打入另册。究其原因,是毛姆对花样百出的“时髦”玩意儿心存警惕,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就英语散文风格嬗变的论述中找到例证。在《散文和神学家蒂乐生》中,毛姆毫不掩饰他对质朴文风的喜爱。他说平实质朴与华丽典雅这两种文字风格“没有对错之分,只有品味之别”,但质朴文字比起华丽风格更适合描述实际事物,“如果你侧重文章主题,也就是你更关注面包与黄油,而非果酱,那么避免华丽文风就能让文字更具说服力”。在毛姆看来,时移世易之后,当年那些紧跟时尚的文章“如今读来不过矫揉造作,华而不实”,而所谓的“魅力”更是可疑,“因为魅力无穷的人往往一无是处”。于是我们便能理解毛姆对蒂乐生何以如此褒扬,这位大主教一生经历王政、内战、护国公、复辟和光荣革命,时代巨变教他抱持谦逊谨慎的人生观,因而其布道词“无华丽辞藻而言简意赅,风格质朴鲜活而又严肃优雅”,虽经数个世纪但读之不仅不枯燥,反而见出真知与趣味,是最值得欣赏的好文章。
毛姆本人常因写作非经世致用的文字而被评论家们贬入二三流,他对受到“全然罔顾时代背景和社会状况”诟病的契诃夫自是惺惺相惜,“作家的职责就是叙述事实然后全部交给读者,让他们去定夺该如何处置”,而不应鼓动艺术家去解决问题。毛姆在此厘定了作家与社会改革家或公共知识分子的界限,反对将小说当作“布道的讲坛”,因为好的小说自己就能说话,不需要别人添油加醋或者标举意义,就如契诃夫“超脱个人悲喜”地描写生活,却让人“强烈感觉到人们的残忍和无知,穷人的赤贫及堕落还有富人的冷漠和自私,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指向一场暴力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