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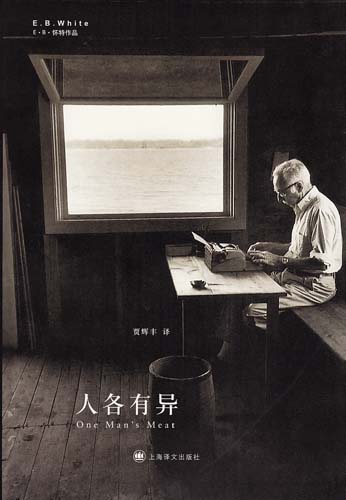 对于离开都市去“他的缅因”、他的乡村小镇、他的农场的怀特来说,他在《人各有异》里所有的发生在农场的一切都是“我之美味,他人之砒霜”,他唠唠叨叨所告知的,都是那些属于农场里的各种各样的农事,关于他的谷仓、他的柴棚、他的农耕诀窍、他的住所,再有就是他的羊羔、他的鸡、他的奶牛、他的猎犬,等等,而属于其同类的人,基本上都是暗影。于他的读者来说,有时候真的感觉怀特的唠叨就如一个乡农一般的烦琐。不过,能让此书畅销不衰的,不是因为他描写这些小事,不是因为他的乡农风格,而是因为读者能在他跳跃性的描述里发现很多属于他独有的特殊看法。比如:当他说:“我下到地面,谷仓风雨不透,和平也得到维持。”接下来的内容都是对二战前夕的评论。也就是说,他可以从对农场里各种小事的描述,直接跳到时事、政治、文化、美学等任何他的思维能跳跃到的方方面面,几乎不需要任何过渡,比如这段的结尾是“美总有个界限,你不能因为会在外表留下瘢痕,就超越了这个界限。和平也是如此。我们如今保有的和平,就如同患有腹膜炎的脱星一样,朝不保夕,令人丧气”,这是与梭罗完全不同的思考方向,也就是说,怀特虽“处江湖之远”却依然忧国忧民。这样亲近时事又这样远离尘嚣,对于读者来说不仅新颖别致,更重要的是感同身受。与之相比感觉类似的梭罗的《瓦尔登湖》则大为不同,梭罗会有极长篇的风景或者动物等细腻描写,用一根看得见或者看不见的脉络连着,让读者可以跟随他,与他沟通,应声附和,虽然他一个人是孤寂的,但他当时的想法却是与他假想的读者是连着的,不曾断开,甚至会让读者感受到他所感受到的更大更广阔的时空;怀特却直接一股脑儿地将他的联想、他的思考结果,坦率地给予读者,不提供联想的路径,让鲁钝的读者会纳闷他的某一个思想是怎么跑出来的?这样有意思的桥段随处可见,你甚至不用猜想怀特下一个要评述的方向,因为不管怎样的农事,他一定会跳跃到上层建筑的层面上去。可以说,着力描写那些琐碎小事,同时又立刻给出结论,不给推导过程的怀特,很有些年轻人未退的童稚和直白。他甚至不关心自己眼界范围之外的一切,虽然他关心时政到了随时随地讨论二战的地步,但他关心身边来来往往的动物,关心远在天边的欧洲,远远胜过了他身边的亲人或者仆人,或者邻居。 对于离开都市去“他的缅因”、他的乡村小镇、他的农场的怀特来说,他在《人各有异》里所有的发生在农场的一切都是“我之美味,他人之砒霜”,他唠唠叨叨所告知的,都是那些属于农场里的各种各样的农事,关于他的谷仓、他的柴棚、他的农耕诀窍、他的住所,再有就是他的羊羔、他的鸡、他的奶牛、他的猎犬,等等,而属于其同类的人,基本上都是暗影。于他的读者来说,有时候真的感觉怀特的唠叨就如一个乡农一般的烦琐。不过,能让此书畅销不衰的,不是因为他描写这些小事,不是因为他的乡农风格,而是因为读者能在他跳跃性的描述里发现很多属于他独有的特殊看法。比如:当他说:“我下到地面,谷仓风雨不透,和平也得到维持。”接下来的内容都是对二战前夕的评论。也就是说,他可以从对农场里各种小事的描述,直接跳到时事、政治、文化、美学等任何他的思维能跳跃到的方方面面,几乎不需要任何过渡,比如这段的结尾是“美总有个界限,你不能因为会在外表留下瘢痕,就超越了这个界限。和平也是如此。我们如今保有的和平,就如同患有腹膜炎的脱星一样,朝不保夕,令人丧气”,这是与梭罗完全不同的思考方向,也就是说,怀特虽“处江湖之远”却依然忧国忧民。这样亲近时事又这样远离尘嚣,对于读者来说不仅新颖别致,更重要的是感同身受。与之相比感觉类似的梭罗的《瓦尔登湖》则大为不同,梭罗会有极长篇的风景或者动物等细腻描写,用一根看得见或者看不见的脉络连着,让读者可以跟随他,与他沟通,应声附和,虽然他一个人是孤寂的,但他当时的想法却是与他假想的读者是连着的,不曾断开,甚至会让读者感受到他所感受到的更大更广阔的时空;怀特却直接一股脑儿地将他的联想、他的思考结果,坦率地给予读者,不提供联想的路径,让鲁钝的读者会纳闷他的某一个思想是怎么跑出来的?这样有意思的桥段随处可见,你甚至不用猜想怀特下一个要评述的方向,因为不管怎样的农事,他一定会跳跃到上层建筑的层面上去。可以说,着力描写那些琐碎小事,同时又立刻给出结论,不给推导过程的怀特,很有些年轻人未退的童稚和直白。他甚至不关心自己眼界范围之外的一切,虽然他关心时政到了随时随地讨论二战的地步,但他关心身边来来往往的动物,关心远在天边的欧洲,远远胜过了他身边的亲人或者仆人,或者邻居。
由此,《人各有异》在我眼里是一本童书,它展现的是一个已经成年却尚未脱离孩子气的年轻人的任性、武断,还有灵动、聪明,而在《人各有异》中,那些灵动和聪明显得那么既具有情趣又有丰富的含义。比如:“要想做一个超国家主义者,先得是一个自然主义者,感受脚下的大地是完整的圆。”他甚至坐在屋里欣赏雪景写专栏的同时还能说出“将美国镌在心里,就像将情书握在手里———它确实意味深长”这样的话,他不停地跳跃性地思考,不停地跳跃式地谈他的农场里的事情,却处处不离他身为撰稿人的职责。梭罗的说理非常透彻,语句也十分精辟。怀特说理同样透彻而且更犀利,但他更在意的是现实,他不停地提到《纽约客》。较之随笔而言,怀特虽然也是随笔大家,但他的随意度远远不够,他受着很大的约束,那就是他的读者可以接受的可读性。
不过,静观怀特的表述,依然会非常欣赏上面已经提到的朝气蓬勃的灵动思考,欣赏他的妙言警句,这些依然是一种舒适的享受。跟从看似逍遥自在实则身心皆负重责的怀特,在他的农场里到处转悠,看他饲养的动物,看他收获的成果,看忙碌在其中的他跳跃性地、真诚地、坦率地、无拘无束地纵横在他从未离开的那些不属于乡村的思绪里,读者会越来越清楚,他在这个农场不会一直待下去,他依然会重返城市,重返那些他心心念念的紫陌红尘。结果是,果然如此。
好在虽然小隐山林,却也别有野趣,怀特在此五年,写完了《人各有异》,以及温暖的《夏洛的网》、《吹小号的天鹅》、《精灵鼠小弟》,并让它们经久畅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