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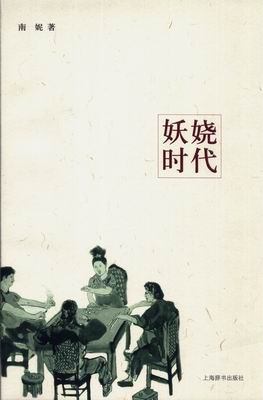 少年时代读毛泽东《沁园春·雪》有过太深的印象,所以当我看到南妮的新作《妖娆时代》的封题,首先想到的不是女性的妩媚,而是山河的壮丽。 少年时代读毛泽东《沁园春·雪》有过太深的印象,所以当我看到南妮的新作《妖娆时代》的封题,首先想到的不是女性的妩媚,而是山河的壮丽。
但南妮笔下的妖娆确确实实在写女性,也是在用女性的特有眼光,把她生活其间的对象,包括精神、物质重新审视一遍。因为是审视,她会像把玩手里的一双高跟鞋一样,触摸女性的思想和意识。就像《妖娆》一篇直接告诉我们的:穿高跟鞋“长时走路虽然艰难”,但“一穿上它,人就挺拔、自信、步调婀娜,说话的速度放慢,声线细了,小动作优雅起来,思想里女性的意识强烈起来”。这富有性感的语句连绵不断,与其说写出了女性穿高跟鞋特有的真实感受,倒不如说她是在想象中,把高跟鞋带给女性性别意识的整体丰富性充分彰显了出来(因为在现实中,穿着高跟鞋的女士在办公楼过道里大呼小叫是屡见不鲜的)。这种彰显,既是自爱,也是为了被爱。虽然她认同“女人最大的心愿就是叫人爱她”,如果竭尽千娇百媚之可能,让男人为之倾倒痴迷,并不过分。但男性因痴迷而付出的代价,却又唤醒了女性的责任意识。所以南妮认为,女性的娇丽与江山的壮丽,在男人心中的权衡,会反过来抑制女性的虚荣。以致她语出惊人道:“辛普森夫人死于温莎公爵之前,或许承担了太多牺牲的爱情是沉重的。如果我是辛普森夫人的话,我肯定是要吓得逃得远远的。如果一个男人把什么都抵押给你,你会多累啊,心累。”(《三十五年》)这样说,并非意味着她做人的低调,更不是给了吃不到葡萄者一个漂亮的说法,而是在现代社会的语境中,浪漫爱有了现实基础,女性的独立意识,渗透进理性思想,平等已经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所以她才会写出《出走》一文,向自己,也向所有的女性追问:“离家出走的女人是过于自信呢,还是因为不自信?”
现代语境中,比如在毛泽东词作中,江山美人作为描写的对象,不再是两种景色的反差,而是互相映射的客观对应物。据此,因“妖娆”一语想到毛泽东的词句,也就不算太离谱。红装素裹,甚至可以顺势借用来形容南妮散文感性与理性的交织。
这种交织,扩展到《妖娆时代》一书中,既是男人与女人对比式关系的体验与思考,也是成人与少年(《第一次火焰》)、俗人与智者(《城市气质》)、穷人与富人(《富人阶层的衍生行业》),国人与老外(《话说老外》)、徒弟与师傅间(《男人们的师傅》),等等双方关系的体悟与反思。
即便性别意识暂时隐退,但笔下有“我”,却是她文章的一贯特色。比如《城市气质》是以描述一个小学五年级生的世博参赛作文而开头的,作文把“我是一个中队长”当中心句,反复申说自己作为一个班干部的作用。让作者摇头叹息的是,小小年纪就以级别意识来看待人事和生活,那他的人生是不会精彩的。作者进而说:“俗人以否定别人来肯定自己。智者肯定能够肯定的一切,也由此增加了生活的丰厚性。”读到这里,我有点疑惑,难道作者不也正是以她的否定来起笔吗?这不是有点自相矛盾吗?看到下文,才发现逻辑一贯的“我”依然在场:“能清楚认识到这点的人似乎并不多。那个写作文的孩子也正是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不过好在他还是个孩子,他还有认识天地宽广的可能。”在否定中留出很大的肯定空间,不是那种折中主义式的两边平衡,而是充分考虑到未来的发展前景,这样的峰回路转,正是“我”的技巧和“我”的思想有机统一。
也许是有意编排,南妮在《妖娆时代》中有了淋漓尽致的言说后,突然以一篇“它们不说话”来煞尾,尤其耐人寻味。
面对其近百篇的散文,跟随其在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多个方面齐头并进,阅读给我们带来的心理起伏,一如在人生阅历中渐趋复杂。但作者南妮呢?也许她生活中有太多的感悟,其内心有太多的涌动,所以需要用一种更具物质化的器具,默默接纳它,或者,干脆消解它。就在这一篇中,她引用了台湾女作家朱天心的话说,佩戴珠宝的女人是为了转移人们对其皱纹的注意。其实,在前一篇《一支烟》中,她写外婆站在阳台上抽烟,说“烟对于28岁即守寡的她意味着什么呢?至少释缓了她难以言说的沉重吧”。我似乎有些明白,如同她外婆的一支烟移开了内心的愁绪,南妮手中的笔,移开了内心的汹涌,把需要在生活中无尽交流而又毕竟难以交流的思想和言语,物化为一本静穆的书。而我们读者,翻过最后一篇,合上全书,把它插回书架时,书以它的近乎冷峻的肃穆,以它的非语言的沉默的力量,成为这个自然世界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