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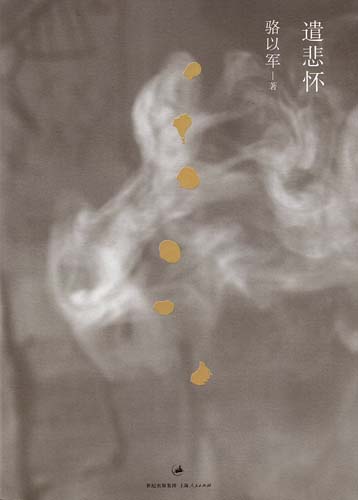 1995年,女作家邱妙津在法国巴黎自杀身亡,这一悲剧触发了作为朋友的骆以军对爱与死亡的思考,《遣悲怀》的写作由此而生。 1995年,女作家邱妙津在法国巴黎自杀身亡,这一悲剧触发了作为朋友的骆以军对爱与死亡的思考,《遣悲怀》的写作由此而生。
如评论家王德威所言,邱妙津以“永远缺席”启迪骆以军对生命的感知参与。骆以军的写作探勘着邱妙津身死的另一面。他以邱妙津的结局作为起步,开始以叙述者的视角追述其身边林林总总的往事,有在小学校园里躲藏在隐秘角落里的游戏,与新婚妻子在香港旅游时的糗事,大学同学阿普的孤儿历程,工作时为女主管代写信函等等。这是现实生活的真切漫漫征途,与半途兀然退出人生形成比照,并无高下之分,只是自我的选择而已。但既低眉于人世间,就要想方设法地排遣这绵延不绝、层层浸染的悲怀,即使不情不愿,也是命定所在。
同学阿普的故事,显然于叙述者有极深的印象,以至其踪影贯穿了许多个章节。阿普在少年时父母猝然离世,留下孤单单一人,他邀请叙述者去自己家的大房子玩,空旷的宅子使叙述者有些茫然若失,不禁想阿普生活在这里是什么滋味,“像被放弃登陆舰坠放进月球引力圈的菜鸟航天员,突然抬头发现母舰被同伴们开走了。只剩下他一个孤零零漂流在彼。”漂流是大家共有的命运,骆以军不仅仅在说单个人。而阿普与父母站在生与死的两界,情形之吊诡与迷茫令人困惑,难以尽言。
然而,在死的那一边却还有喧闹的生。叙述者在产房外焦虑地等待孩子的出世,隔着玻璃看到了婴儿室中的场景,“那些婴孩们在那样寂静明亮的空间里,闭目蠕动着他们的腮。我突然有一种失重晕眩想蹲坐下来的本能,似乎是眼睛无法承受那些婴孩身体反射的某种妖邪幻丽的光照。”“妖邪幻丽”,十分怪异的用词,但置放于死生两界,却又是说不出的合榫。生生死死,处于人生经验的两极,无穷无尽,周而复始。骆以军与亡灵对话,自己选择的是存生于世,不仅忍受着世事的尴尬,还传宗接代,重复生命的循环。邱妙津作为启迪他的缪斯,一旦思索之旅启动,两人对生命态度之大相径庭立时见分晓了。
相较于邱妙津对爱与生命要求完美性和统一性,骆以军自知残缺与尴尬更适合自己的认知。上小学时躲在秘密洞穴里,“试图把时间喊停之计划”以失败告终,昭示着人生路途的无奈;与女友恋爱时的猜忌、等待、沉默、争执,说明对爱不存幻想;在香港摩天大楼上,和妻子两人闹的大笑话是世事无序与尴尬的缩影。骆以军知道自己是无法对生命抱有勘破态度,索性投身其中,以碎裂来对待残缺。
无法忘怀于死,亦留恋于生,骆以军在生命的路途上首鼠两端,不能弃绝任何一方。孔子曾言“未知生,焉知死”,在骆以军这里,即谓“未知死,焉知生”,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在书的末尾,他一家三口来到儿童游乐区的大象溜滑梯,大人站在旁边,“看着我们的孩子,孤单一人的,在那单调的画面里,爬上爬下重复同样的动作。”生命的无趣在于重复,实质上却又无可避免。在孤寂中遣其悲怀,或许就是偷生者所付出的代价也获得的幸福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