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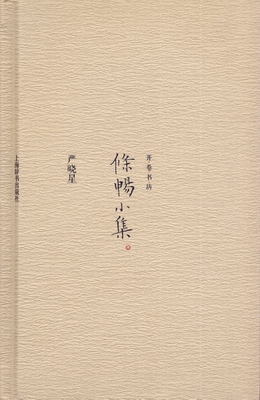 严晓星近年出版了有关古琴的三本书《近世古琴逸话》《梅庵琴人传》《条畅小集》。三书相映成趣:《近世古琴逸话》是掌故,写整个琴坛的琴人的人生片段;《梅庵琴人传》是传记,写一个流派的已故琴人的完整人生;《条畅小集》里的“说琴之什”则多是研究古琴的文章。 严晓星近年出版了有关古琴的三本书《近世古琴逸话》《梅庵琴人传》《条畅小集》。三书相映成趣:《近世古琴逸话》是掌故,写整个琴坛的琴人的人生片段;《梅庵琴人传》是传记,写一个流派的已故琴人的完整人生;《条畅小集》里的“说琴之什”则多是研究古琴的文章。
与琴结缘,说来有趣。严晓星小时候读古典文学作品,总会遇到琴。在描述中,古琴总是一件极其神秘而美妙的东西,有神奇而动人的故事。严晓星就不断想象,时间长了,自然有了拥有古琴、学习古琴的愿望。念大学时,隔壁班的同学听说严晓星喜欢古琴,就说:“我有个朋友会弹琴,介绍你们认识吧。”严晓星说:“不必介绍,南通这么小,说不定哪天就遇到了。”到了1997年,江苏电视台的朋友拉严晓星去参加一个纪念徐立孙先生诞辰百年的活动,果然就认识了这个朋友,发现两人的家只有三分钟的距离。后来,严晓星就跟这个朋友学琴。这个朋友送给严晓星一本《査阜西琴学文萃》,严晓星想:“我学好弹琴就行了,干嘛要去看这些研究琴学的文章呢?”过了不久,严晓星学琴渐渐中断了,想看看琴学的文章,找来找去,空话套话的多,有实质内容的少,最后又把《査阜西琴学文萃》找出来了,还是这一本最丰富,最深入,学到了很多东西。南通是著名古琴流派梅庵琴派兴起的地方,但写梅庵派的文章很有限。到了2002年,严晓星在自学考试,闷得难受就爱乱想,心生一想:“与其期待别人,不如自己动手,搜集整理,写点东西吧。”他一直喜欢历史,喜欢文献,很自然地就偏向古琴的历史与文献研究了。
严晓星现居的南通是一个小城,生活安逸。他的工作是在晚报编辑副刊,每天中午起来,下午去上班,晚上八九点工作完毕回家。深夜通常是他读书和写作的时间,到凌晨三四点休息。写学术文章,搜集材料,考证论证,往往有深夜“破案”的乐趣,他跟朋友说:“昨晚又破了一个案子。”
除目前已出版的三本书外,《七弦古意:古琴历史与文献丛考》也将出版,严晓星还编了多本与古琴有关的文集。他说:“如果从研究的角度来看,我的文章一定是不全面、甚至有重大缺陷的。对我来说,只是在工作之余,对引发我兴趣的话题深入下去,写点心得罢了。更多的是兴之所至,没有严密的研究计划,但愿这点心得还多少有点用处。”
查阜西是古琴界关键人物
时代周报:你自己喜欢古琴,现在正在编“我是怎么喜欢上古琴”的书,为什么要编这样一本书?
严晓星:想起编这本书,是因为和喜欢古琴的朋友初次见面,往往会问:“哎,你是怎么喜欢上古琴的呢?”早先不像现在,喜欢古琴的人很少嘛,遇到了就格外高兴,格外好奇,不知对方是怎么成为自己同道的。后来接触喜欢古琴的人多了,就发现很多有趣的现象。比如,我一个朋友是因为金庸小说《笑傲江湖》,但他总不好意思承认,可能在他心目中,读武侠小说有点丢脸。如果是我,一定自豪地承认,因为我是金庸迷,马上要出一本书《金庸识小录》。
所以,我就觉得,每个人,他们的身份、年纪、经历、时代都不同,接触古琴的过程也不同,写出来,不仅有单个人的故事这样的价值,集中在一起,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时代的变迁,反映古琴传播方式乃至古琴艺术的变迁。于是我先后约请几十位古琴爱好者来写自己爱上古琴的过程,其中有会弹琴的,有不会弹的,有音乐院校古琴专业的,也有民间的琴人,有名家,也有无名小卒,有近百岁的长者,也有十几岁的小朋友,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看着他们的故事,有时候你会觉得,有一件东西,你正在热忱地喜爱,人生该有多么幸福。
时代周报:你在书中多次提到查阜西先生是现代琴学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他在近现代琴史上有哪些重要贡献?
严晓星:从事古琴学术的人,可能会有这样一个感受,就是你经常会和査阜西先生“相遇”。20世纪,最重要的两个古琴团体,南方的今虞琴社,北方的北京古琴研究会,都是以査阜西先生为核心的。査阜西先生还主持过1956年的全国古琴普查和录音搜集,这又是一桩空前绝后的壮举。查先生主持编纂《存见古琴曲谱辑览》《存见古琴指法谱字辑览》《历代琴人传》《琴曲集成》,自己还有大量的古琴著述,《査阜西琴学文萃》是其中的主要部分。他为古琴学术奠定的基础是全面的,对琴学的影响是深远的。曾看到乔建中先生的一篇文章《现代琴学论纲》,其中说到:“查阜西先生在50年代以后为琴学传统的全面恢复,为现代琴学的重建所作的努力……每一事项都具有开拓性和奠基性。”这个说法是完全符合实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