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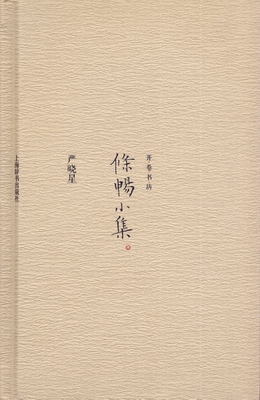 这一半谈琴、一半说书的集子,取“乐琴书以消忧”的意思、唤作《消忧小集》原本最好。可曹孟德那句“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太有名,二十多年前吴祖光先生还编过一本《解忧集》,收录的全是名家“酒话”;就连“消忧”这个词儿,唐诗里不也有“消忧期酒圣”的说法么?可见只要沾上了“忧”,嗜酒的嫌疑是逃不掉的。我没以嗜酒为耻的微意,只怕好这口的读者微醺之际误认了知己,更怕宴席上有仁兄凭这书名儿灌我的酒。何况在很长的一个历史阶段里,个人是不允许有“忧”的,保持着昂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去战斗才是道理,至少也要在阳光下极其满足地成长,消极思想可万万要不得。干脆换个年代早些的出处,刘歆《遂初赋》的“玩琴书以条畅”。“条畅”二字半生不熟:生的人扎眼,反而容易记;熟的人知道怎么回事,作不出离奇文章。还有一条,“撞车”概率不会太高。 这一半谈琴、一半说书的集子,取“乐琴书以消忧”的意思、唤作《消忧小集》原本最好。可曹孟德那句“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太有名,二十多年前吴祖光先生还编过一本《解忧集》,收录的全是名家“酒话”;就连“消忧”这个词儿,唐诗里不也有“消忧期酒圣”的说法么?可见只要沾上了“忧”,嗜酒的嫌疑是逃不掉的。我没以嗜酒为耻的微意,只怕好这口的读者微醺之际误认了知己,更怕宴席上有仁兄凭这书名儿灌我的酒。何况在很长的一个历史阶段里,个人是不允许有“忧”的,保持着昂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去战斗才是道理,至少也要在阳光下极其满足地成长,消极思想可万万要不得。干脆换个年代早些的出处,刘歆《遂初赋》的“玩琴书以条畅”。“条畅”二字半生不熟:生的人扎眼,反而容易记;熟的人知道怎么回事,作不出离奇文章。还有一条,“撞车”概率不会太高。
曾对一个朋友讲,要看一个人的文化、趣味、人生观、价值观甚至胸怀,看他对自家孩子名字的取舍便可知道八九分。给人取名字限制太多,难,给书取名儿容易些,可也不好对付。近百年来,前辈里鲁迅、知堂都是高手,当代则数止庵。他们的妙处都是用最平凡不过的字眼,连缀出最别致大方而见巧思的题目来。我和止庵联系不多,但记得第一次通电话他便夸我给李君维先生取的书名儿《人书俱老》,让我很惶恐,觉得他是客气才这么说。后来好像读过他写的关于书名的文章,最近见面聚餐时他又总和扬之水、谢其章两位不住私语新书的题目,才知道他对此是时在念中,漂亮的书名儿看似妙手偶得,背后也都下足了工夫。
记得又有次和朋友聊天,说我们这样漫无目的毫无章法的读书,正如瓜藤枝蔓,铺展开去,不知在何处分岔,亦不知在哪里终止,不如便写本书,叫作《瓜蔓抄》罢。朋友在电脑那头击键叫好,两人很当回事儿似的谋划了一番。后来又想到“瓜蔓抄”这三个字血腥气太重,将六百年前千万人的血泪惨史化作消遣,终究下不去手,也便作罢。
如今常有给师友的著作取名儿的机缘。辛丰年先生的《处处有音乐》、成公亮先生的《秋籁居琴话》、陈学勇先生的《林徽因寻真》,还有陆蓓容的新书《更与何人说》(原拟《方留恋处》,随即发现香港刘绍铭先生用过了)……有时候想想,作为一个爱书人还是很幸福的——单这几个字的书名儿,便获得了多大的乐趣啊!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