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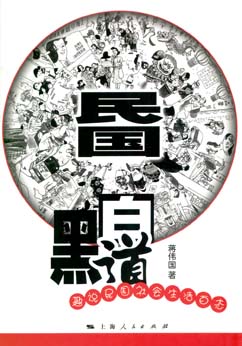 拍卖货物即将倒闭的企业 拍卖货物即将倒闭的企业
拍卖物的第三类是即将倒闭的企业。1934年,中国著名的近代棉纺织企业申新七厂因向汇丰银行借款到期,向国民政府求援无效,只得向汇丰银行申请转期。对此,汇丰竟置之不理,且不经过中国法律手续,强行将申新七厂“估作低价”拍卖,结果被日商竞得。这一事件,引起了沪上各界爱国人士的愤慨,申新各厂职员更是联合行动起来,反对拍卖。慑于各界的强烈抗议,汇丰只得“解除拍卖”,同意与申新七厂签转期合同。1920年,永兴洋行买办吴伟臣为满足永兴扩展蛋品出口、开拓蛋品货源业务的需要,怂恿河南永大蛋厂汪述卿与永兴洋行签订期货合约。汪考虑到数量太大,顾虑订约后蛋价会有变动,且收购货款也非轻易能够凑齐,踌躇再三不肯签约。吴竭力促成,并答应钱款不够可以全数垫借。在吴的撺掇下,汪最后同意了这笔交易。但当汪向产蛋区大批收购货物时,蛋价不断上涨,远远超过了所订的价格。若按约交货,永大将亏损二三万两银子,故要求通融。然而吴伟臣食言而肥,声称国外催货甚急,再三逼汪履行约定。此时汪已无力如约交货,最后只能把永大交上海法商三法洋行拍卖,抵偿吴伟臣所垫全部借款本息和由于违约应付给永兴的全部损失。
与申新七厂、永大蛋厂相比,大中华纱厂的命运要幸运得多。大中华纱厂于1916年由聂云台发起创办,占地147亩,厂房建筑和机器设备都比较完善,可纺32支以上的细支纱,还有一套自备发电设备,曾被同行赞誉为“模范工厂”。刚开工之时,大中华纱厂的经营颇有活力。不料下半年情况急转直下,原棉价格剧升,造成棉纱大量积压;加上当时英镑汇价回升,而聂云台向洋行订购机器的款项大部分还未结汇,由此他又亏蚀了一笔巨款,只能用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维持工厂开工。到1924年,大中华纱厂的债务已高达176万两白银,加上利息,总数达190万两。由于债台高筑,聂云台再也无处借到款项了。于是,债权人接管工厂,并登报限价,194万两白银拍卖该厂。
大中华纱厂要被拍卖的消息传出后,沪上的很多实业家跃跃欲试,力图购得该厂产权。经过一番竞争,后来发展成为全国第二大私营棉纺织企业的永安纺织公司最终以159万两白银的价格收购了大中华纱厂。
非常奇特的拍卖 拍卖白俄妇女
除了上述三类正常的拍卖外,民国时期还出现了一种非常奇特的拍卖:妇女拍卖。不过,这样的拍卖,实在是走入了拍卖的死胡同。
民国时期,流寓在上海的白俄甚多。由于他们奔赴异国他乡,并无合理的动机,其中的一些人就被送进了收容所。然而收容所毕竟不是慈善机构,它供养不起太多的被收容者,于是在静安寺的一家收容所里,出现了拍卖俄罗斯妇女的事。拍卖者规定,每名白俄妇女,不论高矮、胖瘦、妍媸,均为30元。凡有意求购者,只要付足钱款,即可隔着大布幔任选一人带走。至于求购者将所买的白俄妇女立为正妻还是纳为侧室,拍卖者概不过问。
拍卖动因 生存、发展、发横财
民国时期的各类拍卖活动,不仅拍卖的对象各不相同,且卖主提供货物出卖的原因也互有差异。其中最主要是货主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
溥仪退位以后,民国政府参照宣统三年内务府预算,规定每年拨出400万两白银,作为逊清皇室的经费。这笔费用,虽比清帝退位前749万两的皇室经费预算大为缩减,但是对于民国政府而言却是一个沉重负担。故而除民国元年外,民国政府每年都不能按数拨交。1916年,逊清皇室实际只领到了153万两。民国政府欠拨逊清皇室的经费愈来愈多,使皇帝的日常生活日益难以为继。租房卖地、压缩机构、精简人员以节约开支都无济于事,溥仪就以拍卖宫藏文物来苟延残喘。
与维持生命延续的基本欲求不同,有的拍卖活动是为发展社会事业而举办,其动机要高尚得多。林森在临终之时,特地对其所藏文物作出过安排。他在遗嘱中说:“余身后,将手置庐山、北平、南温泉及南京房屋,暨存款、衣服、字画、古玩变价,作为创办若干职业学校基金……”他的家属就林森所收藏文物进行的拍卖,即是按林森的临终嘱托办的。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四行二局”曾设立了一个名为“代理出售政府物资资产委员会”,专门对大宗物品和战争遗留物资进行拍卖。这类拍卖的动因,与上述两种拍卖的原因显然有很大差别。当时,不少拍卖行,特别是上海的拍卖企业,在对日伪敌产、美国剩余物资所进行的拍卖活动中大发横财,狠狠地赚了一笔。
民国时期,人们对拍卖业大多抱贬抑的态度。在《上海竹枝词》中,这类描写并不少见:“订期叫货也称行,又唤两人拍卖行。存积太多思脱尽,能开此法变钱忙。”“市井争开拍卖风,宜今宜古各流通。好将垄断翻新样,不在区区划一中。”这些对上海市井的真实记录,反映了人们对拍卖业的不满乃至反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