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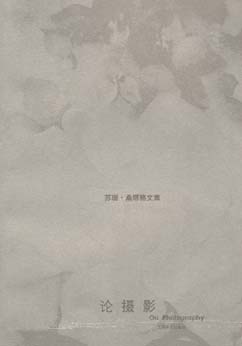 摄影在二十世纪政治斗争中的作用和地位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苏珊·桑塔格在《论摄影》(黄灿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1月)中,对摄影的政治敏感首先是从摄影作为一种政治监控和证据的角度体现出来,她提到一个历史事实——“从一八七一年六月巴黎警察用照片来大肆搜捕巴黎公社社员开始,照片就变成现代国家监视和控制日益流动人口的有用工具。”(第5页)当年学习巴黎公社史的时候,我并没有留意过这一重要细节,近日重新找出当年最主要的两部读物来查找相关的史料。一部是法国记者阿尔蒂尔·阿尔努的《巴黎公社人民和议会史》(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9月),作者是公社委员,在流亡瑞士期间写成此书。另一部是法国新闻工作者和历史学家普·利沙加勒的《一八七一年公社史》(柯新译,人民出版社,1962年2月),作者也亲历了巴黎公社斗争,后流亡英国,在马克思的帮助下写作本书。可惜的是,在这两部亲历者的著述中没有找到以摄影照片搜捕公社社员的记述,桑塔格应该有其他的参考史料。她说,“相机的一个用途,是其记录可使人负罪”,“一张照片可作为某件发生过的事情的不容置疑的证据”(第5页)。这是肯定无疑的,我们都还记得在1976年的“四五运动”中,“四人帮”就是通过照片来抓捕那些在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讲的学生和工人。当然,摄影的政治监控和记录无疑是一把双面刃,谁也不知道因照片而敲起的丧钟最终是为谁而鸣。桑塔格在本书的“引语选粹”部分还引述了南非摄影师阿尔夫·库马洛的一段话:“……突然,我身边一个小男孩倒在地面上。那时我意识到警察不是在鸣枪警告。他们是在向人群开枪。更多的孩子倒下。……我开始拍摄我身边那个临死的小男孩。……我说我是记者,在这里记录发生的事情。”(第190页)这是摄影作为见证的力量最突出的例子。 摄影在二十世纪政治斗争中的作用和地位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苏珊·桑塔格在《论摄影》(黄灿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1月)中,对摄影的政治敏感首先是从摄影作为一种政治监控和证据的角度体现出来,她提到一个历史事实——“从一八七一年六月巴黎警察用照片来大肆搜捕巴黎公社社员开始,照片就变成现代国家监视和控制日益流动人口的有用工具。”(第5页)当年学习巴黎公社史的时候,我并没有留意过这一重要细节,近日重新找出当年最主要的两部读物来查找相关的史料。一部是法国记者阿尔蒂尔·阿尔努的《巴黎公社人民和议会史》(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9月),作者是公社委员,在流亡瑞士期间写成此书。另一部是法国新闻工作者和历史学家普·利沙加勒的《一八七一年公社史》(柯新译,人民出版社,1962年2月),作者也亲历了巴黎公社斗争,后流亡英国,在马克思的帮助下写作本书。可惜的是,在这两部亲历者的著述中没有找到以摄影照片搜捕公社社员的记述,桑塔格应该有其他的参考史料。她说,“相机的一个用途,是其记录可使人负罪”,“一张照片可作为某件发生过的事情的不容置疑的证据”(第5页)。这是肯定无疑的,我们都还记得在1976年的“四五运动”中,“四人帮”就是通过照片来抓捕那些在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讲的学生和工人。当然,摄影的政治监控和记录无疑是一把双面刃,谁也不知道因照片而敲起的丧钟最终是为谁而鸣。桑塔格在本书的“引语选粹”部分还引述了南非摄影师阿尔夫·库马洛的一段话:“……突然,我身边一个小男孩倒在地面上。那时我意识到警察不是在鸣枪警告。他们是在向人群开枪。更多的孩子倒下。……我开始拍摄我身边那个临死的小男孩。……我说我是记者,在这里记录发生的事情。”(第190页)这是摄影作为见证的力量最突出的例子。
台湾学者陈传兴的《银盐热》(行人文化实验室出版,2009年2月)是一本摄影史论与台湾社会历史研究交织在一起的文集,其中的《见证与档案——试论美丽岛事件之影像纪录》深入地探讨了摄影作为见证和监控的政治与法律作用。在历史的活动中,摄影的介入完全是一种预定的见证行为。作者说无论是官方或私人的摄影,虽然意向目的不同,但是却共同建造着这个历史事件的“见证共体”,每张影像都沾染着历史性暗影,似乎都在召唤着某种“审判”(第90页)。但这里的“见证”并不仅仅是我们通常所讲的那种语义,而是有着更尖锐、更凝重的意义:法律——“在这过程中‘摄影’即‘法律’,‘见证’的意义就在此产生”(第90页)。除了在法庭上作为呈堂证物之外,摄影在审讯中也被作为精神心理刑求的手段工具而运用。美丽岛事件的当事人后来以小说的方式追述了审讯中的影像运用:以被枪毙的死刑犯照片威胁被审讯者;以拍摄被审讯者的遗像的方式来制造恐惧感;摄影成为逼诱供词的手段。作者指出,在这次大审判的三十三人中,有几位是以照片作为刑判证据的,而三十三人中唯一被免刑者则是以照片中“无该被告影像存在等情”为事实依据。被以照片作为证据的嫌疑人在答辩词中有这样的说法:“因为警方有我拿大旗的照片,我才去自首说明真情”、“承认带木棍游行……刚好被照到相”、“当时曾被人拍下照片,我是面向群众劝解他们”……可见摄影“见证”的法律意义。
在事件之后,影像的保存、藏匿就成了极为敏感和危险的事情。当事人陈博文说当时把照片洗出来后就把底片丢掉,只保留了比较关键的二三十张照片。作者说,这是令人不解的:底片不是更容易秘密藏匿、携带吗?而且,见证需要流通,流通需要复制,取消了底片就是取消了这种可能。作者的思考是:“销毁底片,见证了见证者要回到现场,回到那个不可能重复的历史片刻欲望,没有人能够替代他自己的亲身体验,永远独一无二的秘密……”(第114页)而情治单位的逻辑和价值观却是相反的,它会以高价安排摄影、收买底片,去建立为了政治审判而需要的秘密指证档案。作者在本书的“序”中说:“摄影与历史,书中这几篇文章的意图;另一种摄影史。”这可能是最吸引人、最能够震撼人的灵魂的摄影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