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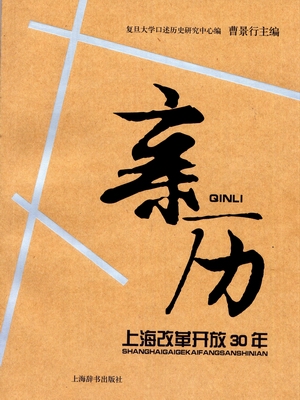 20世纪80年代初,时任上海教育局顾问的吕型伟“冒天下之大不韪”,率先对“全国一张卷”的高考制度提出质疑,在他的努力下,上海在全国范围内第一个走上了高考自主命题、自主招生的道路…… 20世纪80年代初,时任上海教育局顾问的吕型伟“冒天下之大不韪”,率先对“全国一张卷”的高考制度提出质疑,在他的努力下,上海在全国范围内第一个走上了高考自主命题、自主招生的道路……
人物名片
吕型伟 1918年生于浙江省新昌县。1956年起任上海市教育局教研室主任,兼普教处处长和政教处处长等职,后调中央教科所任研究员。1966年回上海市教育局,任副局长、顾问。1988年离休。现任上海教育学会名誉会长,全国中小学课程改革总顾问等职。
上海为何考了个“王老五”
解放初期,除了北大、清华等少数几所高校实行非实质性的联合招生外,全国绝大多数高校仍沿袭旧制,实行单独招生考试。招生的计划、条件和办法都由各校自行决定。1952年教育部明确规定,自该年度起,除个别学校经教育部批准外,其余高等学校一律参加全国统一招生考试。至此,统一高考制度基本形成。这样,全国统一命题、各省市按招生名额划定录取分数线成了一种惯例。
解放前,我就在上海教书;解放后,担任上海市东中学的校长,后来又调到市教育局任教研室主任、普教处处长等职。我对全国统一高考发生疑问是从1959年开始的。那年的全国高考,福建最低录取分数线是全国最高的,位列第一名;上海排第五名。上海分管教育的市委书记说,上海条件这么好,怎么考了个“王老五”?他对这个名次很不满意,让我带一批校长去福建取经。
在福建考察之后,我发现,上海考大学的最低录取分数线之所以比兄弟省市低,是因为上海高中毕业生少而大学招收的名额多。录取比例高,录取分数线自然会低一些。另外,我也发现,不少地区学生的高分是靠加班加点、死记硬背考出来的。我到北大、清华进行了跟踪调查,发现上海学生的高考分数虽然不比其他学生高,但进入大学后的发展潜力绝不比别人差。上海的学生知识面广,活动能力强,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强,就是死记硬背的本事比不过人家。
这样我心里就踏实了。分管的市委书记听了我的汇报以后,也放心了。这次的学习和调查后,我一直在考虑教育成果如何评价才能公允,怎样才能对教育改革有利。这样一考量,思路很自然地集中到了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设置课程教材,要对现行的高考制度进行改革。
“蹲点”南师大附中教改
1964年春节,毛泽东同志在一次座谈会上对当时的教育现状进行了批评,认为学生负担过重,课多、书多,考试以学生为敌人,搞突然袭击,是摧残学生。这就是著名的“春节谈话”。我当时已被调到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部要我带一个专家小组到基层去实践谈话精神,于是我带了一个三人小组到江苏省南师大附中去蹲点调查。那里正在进行一场轰轰烈烈但又有争议的教育教学改革。我听了半年课,发现老师被晾在一旁的次数不少。同学们也没有异议,因为大家都已形成共识:老师也不是什么都懂。那是一种让学生充分展示个性、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
我们调查组一致认为南师大附中的改革是成功的。到了暑假,省教育厅副厅长召开了一个全省中学校长会议,介绍这所学校的教学改革情况。会议一开始进行得很顺利,没想到在接近尾声时,省委宣传部和教育厅的主要领导来到会场,全盘否定了南师大附中的改革经验。我则公开支持南师大附中的改革。
我让该校数学、物理、语文三门学科的教研组组长写了三篇介绍教学改革的文章,加上学校写的一篇,一并推荐给《人民教育》期刊。《人民教育》破例在同一期上登了这四篇同一所学校的文章,几乎是给南师大附中出了一期专刊。
这些经历,为我后来在全国倡导课程教材改革以及进一步提出改革高考制度打下了思想基础。
从一纲一本到一纲多本
1977年9月,教育部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提议,决定恢复中断十一年的高考。仓促之间,“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采取了每省单独考试招生的方式,全国1000多万人涌进考场,27万余人被录取。
1978年,高校招生走向规范,又开始实行全国统一命题,统一考试时间。当时的工作重心是恢复和重建在“文革”中被中断和打乱的教育教学制度和秩序,课程教材改革和相应的考试制度改革还提不上议事日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全国统一命题、统一考试的弊端重新显现了出来。
1978年冬,我以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的身份到法国访问。以后我接连去了日本、美国考察。国外先进的教育教学理论和技术拓宽了我的眼界和思路。我把课堂教学称为传播知识的第一渠道,将课堂教学以外的信息渠道称为第二渠道,提出二者应该并重。我于1983年发表一篇题为《改革第一渠道,发展第二渠道,建立两个渠道并重的教学体系》的文章。
文章发表后,引起了轩然大波。从上海市到教育部,不少教育界的领导公开表示反对。当时改革开放不久,被长期禁锢的思想一下子打开,有些同志一时难以适应,也是可以理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