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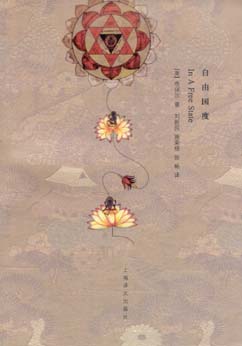 为检测文学出版业编辑的水平,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曾做过一个实验:他们把某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一部重要作品(曾获布克奖)第一章换用假名,寄给了20家英国出版社,结果所有出版社审稿编辑都发出了退稿信。这一实验,简直成为文学领域一个小小的“索卡尔事件”。评论界对此唏嘘不已,大叹编辑的鉴赏力有问题。 为检测文学出版业编辑的水平,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曾做过一个实验:他们把某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一部重要作品(曾获布克奖)第一章换用假名,寄给了20家英国出版社,结果所有出版社审稿编辑都发出了退稿信。这一实验,简直成为文学领域一个小小的“索卡尔事件”。评论界对此唏嘘不已,大叹编辑的鉴赏力有问题。
被《星期日泰晤士报》拿来做实验的,就是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V.S.奈保尔,和他的代表作《自由国度》(In a Free State)。诚然,奈保尔的实力毋庸置疑,然而《星期日泰晤士报》选择奈保尔,选中他的《自由国度》,恐怕也是费过一番心思的。《自由国度》的叙事极其稳重克制,几乎不涉情感和判断,力道缓缓发挥,更没有先声夺人之势。实验始作俑者寄出第一章时,出版社编辑的被涮,恐怕已在预料之中。
《自由国度》包括序曲、尾声、两个中篇和一个长篇共五个故事,均以异族之间的文化冲突为主题。中篇《孤独的人》和《告诉我,杀了谁》说的都是第三世界青年到英美两国打工的故事。逼仄的住房、超负荷的工作、与老鼠为伴的生活、银行里慢慢上涨的存款数额、文化差异带来的尴尬和灼痛,让人不禁联想到35年后也获布克奖的印度女作家基兰·德赛笔下的《失落》。虽则后者对本族文化感情颇深,而奈保尔更认同大不列颠风气,但这两个中篇背后的东西,却和《失落》有太多相似。当然,奈保尔写这些打工仔,似不如德赛生动亲切,反而有些刻板,多多少少在迎合一般人对第三世界打工仔的期待,让人想起那些从小在国外长大的华裔作家笔下的中国。
篇幅占去大半的长篇《自由国度》,是这本书的重头戏。某非洲国家内乱期间,殖民政府的公务员鲍比,在去异地参加一次会议后,和同事的妻子琳达一同驱车返回工作地。琳达身上多是殖民者的优越、冷漠和谨慎,鲍比却更同情黑人。琳达的言行让鲍比恼火,鲍比善待黑人的良好远望却总难实现。琳达在旅途中期待一次婚外关系,同性恋的鲍比却想和一名黑人男孩达成交易。琳达在患难之际表现出女性特有的温存,鲍比却在屡屡受挫之际对黑人大为光火。二人的状态不经意间发生了有趣却又符合逻辑的逆转。
一路上,他们遇见了形形色色的黑人:小兽一样的孩子,被军队伙食养得膘肥体壮的士兵、牛马一样受奴役的仆人、羔羊一样待宰的平民……经历了殖民时代的非洲,甘受压迫者有,残忍自负不亚于殖民者的也有。正如故事里的上校——一位态度强硬的殖民者所言:“他们说任何地方都有好人和坏人。可在这里没有好坏之分。他们只是一群非洲人。他们为所欲为。你得记得这点。你无法去恨他们,甚至你无法对他们生气。无法真的生气。”把这句话里的“非洲人”换成“人”,算是这篇小说力图描写的一种状态。
至于“自由”,正是奈保尔虚构的这个“自由之邦”里影儿都没有的东西。殖民者行将离开时的内乱给非洲人带来的灾难自不必说,连条件优越的白人公务员,连怀着善意到非洲寻求心灵家园的鲍比,都只落得满身伤痛。自由,在缺乏根基的国度,某种意义上意味着混乱。奈保尔式的反讽,最终着笔于鲍比的心态,那便是“我一定要离开”和“我一定要炒卢克(按,故事中鲍比的童仆)的鱿鱼”之间的焦灼。
在同是来自第三世界的诺奖获得者库切眼中,非洲是一块罪恶之地。他在《青春》里写道,“如果明天大西洋上发生海啸,将非洲大陆南端冲得无影无踪,他不会流一滴眼泪。”奈保尔《自由国度》中的南非,则是一片爱和恨都没有依托的无奈之乡。无怪乎奈保尔笔调冰冷,不着任何明显的情感色彩。这种节奏缓慢、立场不明朗的作品,不受当代读者和编辑的喜爱,似不为怪。《星期日泰晤士报》算是打了一张必赢的牌,至于当代文学出版编辑的水平究竟如何,大概还得另找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