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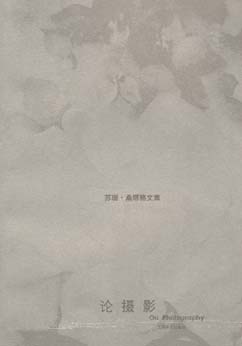 中文读者读苏珊·桑塔格《论摄影》一书首先遇到的是对译本的信任问题。当然,所有译作都会遇到这个问题,但是由于苏珊·桑塔格思想的深刻性和行文中总是具有一种冷峻、犀利的风格,译者对原文的理解是否正确和译笔的恰当与否会使译文的可信度成为更突出的问题。我手头只有新出版的黄灿然译本,译者在后记中提到多年前某译本是“谬误百出”,我想这应该是可信的。但是,我认为译事难有完美,即使是较好的译文也难免会有小疵。即以黄译本为例,全书正文第一句话中的“无可救赎地”就未必很妥帖——原文中似乎并没有因不信上帝而无可救赎的意思,我想或许“冥顽不灵地”甚至更简单的“依旧不变地”会更准确些?另外,“影像”还是“映像”,哪个更符合柏拉图的洞穴说?可能也值得再思考。说这些并非要在黄译本中挑刺——本文就是依据该译本而写的,只是想说明在我这个译事的门外汉看来,翻译是何其艰难的事情。 中文读者读苏珊·桑塔格《论摄影》一书首先遇到的是对译本的信任问题。当然,所有译作都会遇到这个问题,但是由于苏珊·桑塔格思想的深刻性和行文中总是具有一种冷峻、犀利的风格,译者对原文的理解是否正确和译笔的恰当与否会使译文的可信度成为更突出的问题。我手头只有新出版的黄灿然译本,译者在后记中提到多年前某译本是“谬误百出”,我想这应该是可信的。但是,我认为译事难有完美,即使是较好的译文也难免会有小疵。即以黄译本为例,全书正文第一句话中的“无可救赎地”就未必很妥帖——原文中似乎并没有因不信上帝而无可救赎的意思,我想或许“冥顽不灵地”甚至更简单的“依旧不变地”会更准确些?另外,“影像”还是“映像”,哪个更符合柏拉图的洞穴说?可能也值得再思考。说这些并非要在黄译本中挑刺——本文就是依据该译本而写的,只是想说明在我这个译事的门外汉看来,翻译是何其艰难的事情。
摄影与政治监控
全书包括有作者本人六篇文章和一篇由作者从名家著述中摘引出来的“引语选粹”。译者认为,“在这本著作中,桑塔格深入地探讨摄影的本质,包括摄影是不是艺术,摄影与绘画的相互影响,摄影与真实世界的关系,摄影的捕食性和侵略性等等。”;“对于读者而言,这本书的丰富性和深刻性不在于桑塔格得出什么结论,而在于她的论述过程和解剖方法”(见“译后记”)。这些概括与分析我认为是对的。但在我的阅读中,更感兴趣的是作者关于摄影的政治叙事与道德感的论述,其中有些问题更与我们的公共领域的形成大有联系。
桑塔格对摄影的政治敏感首先是从摄影作为一种政治监控和证据的角度体现出来——“从一八七一年六月巴黎警察用照片来大肆搜捕巴黎公社社员开始,照片就变成现代国家监视和控制日益流动人口的有用工具。”(第5页)当年学习巴黎公社史的时候,我真的没有留意过这一重要细节,但是那时候我们都还记得在伟大的“四五运动”中,“四人帮”就是通过照片来抓捕那些在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讲的学生和工人。当然,摄影的政治监控和记录无疑是一把双面刃,谁也不知道因照片而敲起的丧钟最终是为谁而鸣。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这些照片又成为了人民胜利的历史画卷中最感人的篇章。以后还有更多的风雨中的故事、更多的广场上的人流与面孔,桑塔格说,“相机的一个用途,是其记录可使人负罪”,“一张照片可作为某件发生过的事情的不容置疑的证据”(第5页)。的确是这样,因此在人类政治史上,常有子弹在黑夜中向摄影闪光灯闪起的地方密集地射去——在直到今天的摄影史上,这些场景仍会使很多亲历者痛苦难眠,仍会使闻者感到震惊和悲愤,同时也证明了摄影的力量。桑塔格在本书的“引语选粹”部分引述了南非摄影师阿尔夫·库马洛的一段话:“……突然,我身边一个小男孩倒在地面上。那时我意识到警察不是在鸣枪警告。他们是在向人群开枪。更多的孩子倒下。……我开始拍摄我身边那个临死的小男孩。……我说我是记者,在这里记录发生的事情。”(第190页)对此我们这一代人会无动于衷吗?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的历史社会学著作《民族——国家与暴力》早已全面地论述了最大化的监控与极权统治的关系,他把包括摄影手段在内的监控看作是国家权力的生产过程:“信息储存、核计和传播的电子方式,已越来越侵入这个时代,积累与政治活动有关的信息的前景似乎没有尽头。在现代的、和平的国家里,信息控制连同极其迅捷的通讯、交通体系以及复杂的隔离技术,能够直接用于监视人的一举一动,因而生产出高度集中的国家权力。”(第359-360页,三联书店1998)数码摄影的发展和运用完全证实了吉登斯的分析。在今天,公开地以监控为目的的摄影无处不在,公共安全与政治监控更加密不可分。虽然桑塔格没有像吉登斯那样全力关注监控的问题,但在本书的《影像世界》一文中对于安东尼奥尼拍摄的记录片《中国》的讨论中,也谈到了摄影在中国的政治意味及其与美学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