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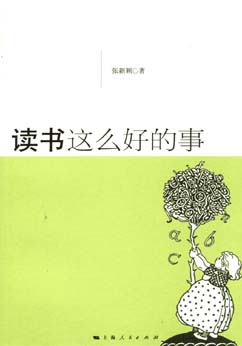 《读书这么好的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版)——只看名字,也许你大抵就能猜到作者是多么感性的一个人。读书,这件已经被无数人谈论过、并注定还将谈论下去的事,多见的是被人们用种种或宏大或华丽的词汇描述,却鲜见有人将之轻轻归结到一个“好”字上去。然而你细想想,这偏又是最深情的一个字眼呢;譬若我们生命过往中深爱已极的那个人,纵有千言万语,怕也抵不过“他真好”这三个字来得情深意切吧。 《读书这么好的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版)——只看名字,也许你大抵就能猜到作者是多么感性的一个人。读书,这件已经被无数人谈论过、并注定还将谈论下去的事,多见的是被人们用种种或宏大或华丽的词汇描述,却鲜见有人将之轻轻归结到一个“好”字上去。然而你细想想,这偏又是最深情的一个字眼呢;譬若我们生命过往中深爱已极的那个人,纵有千言万语,怕也抵不过“他真好”这三个字来得情深意切吧。
为何读书、怎样读书、读书的乐趣究竟何在,这一连串足可以教人侃侃而谈的大题目,在这本小书里却被化作为许许多多诚恳亲切的“感受”,而非高高在上的“观点”、“理论”或“意见”。作者张新颖说,很多人读书,急于做的事情是,当一本书读完时,要对他的感受进行概括、提炼、总结;但他却希望人们不要急于去形成“意见”和“看法”,而尽可能将读书过程中那些“零星的、你说不清道不明的感受”保持得长久一点,“让感性的那个东西保存得长久一点”,并努力去保护和珍惜它。上过张老师课的学生大概都知道,他自己就是这样一位不折不扣的“感性学者”——从文字到语言。你很少从他嘴里听到艰涩高深的理论术语,多的却是从容亲切的“故事”。他常常在讲完一段话之后习惯性地加一句:“我要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他的那些个“意思”,有时候是零碎的、未经修剪的,甚至有时候,他会讲着讲着突然停下来,发一会儿呆,然后出人意料地说:“哎呀,这个我也说不好。”或许正是因了这诚实吧,他所讲述的那些一点儿也不咄咄逼人的“感受”,常常竟能一句句直逼到人心里去。
谈及人与书的关系,作者给出的词汇是:亲密与美妙,还有幸福。他说,有些人与书打了一辈子交道,和书的关系不能说不好,但这“好”却一直停留在普通关系阶段,“友好,礼貌,保持着适当的距离”。然而真正爱书的人却不是这样。法国作家格拉克将《红与黑》视作自己的“文学初恋”,认为那是一种“野性的、心醉神迷的、排他的恋情,任何其他恋情都不能与之相比”;德国思想家本雅明则认为自己从来不是在“阅读”书籍,而是“住在书里面”,在文字与文字、行与行之间闲荡;而英国作家乔治·吉辛则因经年累月的阅读,感到那些熟悉的书籍染上了可惹起人“追忆往事的香味”:“我只要把鼻子凑近这些书,它们那散发出来的气味就立刻勾起我对往事的种种回忆。”在这里作者试图告诉我们的是,人和书的交流与人和人的交流是一样的,书并非被动的客体,而是可以让我们与之相爱、沟通,甚至共同成长的。你抛却那些功利的念头,心无旁骛地随着它欢笑、哭泣、争论,单纯地爱上它,它才会给你亲密、美妙与幸福;“你对书好,书就会对你好”。
当然,感性地读书、爱书,并不等于就应当随心所欲,一味由着自己好恶来。比如,我们习惯陶醉于阅读中一路无阻滞的快乐,遇到障碍和困难便觉非常扫兴,久而久之,对那些“太难,太费力气,不好懂,不轻松,不好玩”的文字丧失了阅读和思索的热情。然而作者认为,这无异于可能放弃了从这些书中获得的更高、更大、更深的快乐。因为阅读高于自己已有水平的书,就像向高明的人请教,而遇到的那些障碍则正是对我们思考与想象能力做出的挑战。这个时候,迎面走向那些“不懂”的召唤,学会耐心与问题相处,并试着克服它,也许你才会体会到突破和提升自己的大的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