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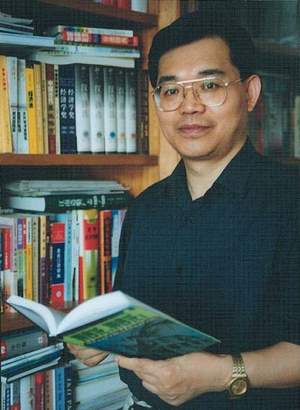 从市场需求的角度看,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引进海外的文化资源,以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这无疑也是一种理性的行为,本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今天的中国已经站在了历史的转折点上,那就是我们已经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并向全世界庄严承诺要逐步开放我们的文化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依然顺从于市场“短视”的本性,不从长远发展的高度来看待文化创新对于产业发展的重要性,不花大力气来培养整个民族文化创新的能力,那么就不仅是文化产业长期发展乏力的问题--中国音像业由于过度引进而导致原创能力衰退濒于困境的现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更严重的是,我们中华民族也可能因此而无法真正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文化毕竟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证,没有这个身份证,我们如何通行于世界各地? 从市场需求的角度看,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引进海外的文化资源,以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这无疑也是一种理性的行为,本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今天的中国已经站在了历史的转折点上,那就是我们已经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并向全世界庄严承诺要逐步开放我们的文化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依然顺从于市场“短视”的本性,不从长远发展的高度来看待文化创新对于产业发展的重要性,不花大力气来培养整个民族文化创新的能力,那么就不仅是文化产业长期发展乏力的问题--中国音像业由于过度引进而导致原创能力衰退濒于困境的现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更严重的是,我们中华民族也可能因此而无法真正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文化毕竟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证,没有这个身份证,我们如何通行于世界各地?
我们强调培养民族文化的创新能力,并不意味着不需要遵循产业发展的规律,也不意味着要把文化创造的成果置之于书斋;恰恰相反,当我们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待文化创新能力的培养时,当我们把原创文化的成果纳入产业发展的轨道时,那么涌现出的将是何等壮观的生产力啊。日本等发达国家在处理这一问题时的做法确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写到这里,不仅回想起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学界曾就“人文精神寻思录”展开过一次较大规模的讨论。当时的背景是,经济体制的转轨,经济结构的调整,新的要素市场的出现,新的投资机会的大量涌现,吸引着许多中青年学人以功利为主导,热衷于从事“咨询”、“对策”等技术性、实物性的研究,忽略了对人文精神的追求,对公共的关心,对人类终极目标的关怀。由此,当时学界有识之士的呼吁之一便是,在市场经济的面前,文化界应有对知识和文化的信念,对真理和道义的担当,对人类命运和前途的关心,对中国文化建设的不懈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一次的讨论总体上是积极的、建设性的。
今天,随着多哈会议的槌声,我们已经跨过了WTO的门槛。随着文化市场的开放,外国资本的进入,中国的文化产业将面临更多的挑战和机遇,与此同时,如何培养和提高民族文化的创新能力,建设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任务,较之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更加紧迫地放在我们的面前,急待我们去努力,去实践。与90年代初中期不同的是,今天我们对文化的关怀不应该再是冲动的、情感的,而应该是有内容的,负责任的,考虑后果的(注6),而且还应该把文化创造的成果通过不同的方式,直接地、间接地同产业发展结合起来,以此进一步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准。这就是我们这一代文化工作者的光荣使命。
注释:
注1、3、4参见陈昕 :《WTO与中国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
注2参见楚天舒、杨贵山:“美加杂志纠纷始末”,《中国图书商报》,2001年1月9日。
注5M. Potter,“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1990.
注6王元化、胡晓明:“关于人文知识分子与21世纪的对话”,《上海文化》,2001年改刊号。
草于2001年12月11日深夜
定于2002年1月1日
(本文作者系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社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