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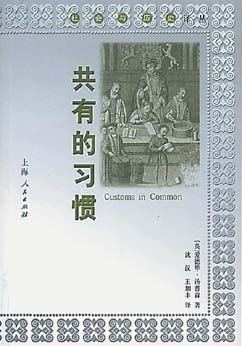 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性”是先天的,普遍的;“习”是后天的,特殊的。两者孰轻孰重?这大概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不过“性”和“习”不能完全割裂开来讨论。人类历史上的无数次战争起于对立的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都属“习”的范畴),但也是人的贪婪本性使然。现今强调“认同”或“文化身份”的论者可能相信,“习”不仅是差异性和多样性的保证,甚至还是“性”的决定因素。有常言为证:“习惯成自然”,“习久成性”。确实,“习”的力量深入而持久,人们往往深处其中而不自知。 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性”是先天的,普遍的;“习”是后天的,特殊的。两者孰轻孰重?这大概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不过“性”和“习”不能完全割裂开来讨论。人类历史上的无数次战争起于对立的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都属“习”的范畴),但也是人的贪婪本性使然。现今强调“认同”或“文化身份”的论者可能相信,“习”不仅是差异性和多样性的保证,甚至还是“性”的决定因素。有常言为证:“习惯成自然”,“习久成性”。确实,“习”的力量深入而持久,人们往往深处其中而不自知。
然而,也有人轻视习惯的力量。梁启超在《开明专制论》一文写道,某些18世纪思想家“迷于空华,醉于噩梦”。他们有舍我其谁的气概,“视国家为器械,吾欲制之则制之,欲改之则改之,吾凭吾心之规矩,以正其方圆”。这类人物尊崇普遍的人性和普遍的理性,抱负远大。在他们设计完美的鸿图里,不见社会习俗的踪迹,于是行之于甲地的制度必然可以移植于乙地。上世纪20年代,马寅初先生在清华的一次演讲中批评那些不顾中国习惯的归国留学生,他们“遇时不好时,就要改革,卒至改革不行,必至失败灰心”,颇类似于《宋名臣言行录》中记载的薛奎:“性刚毅,既与政,遂欲绳天下一入于规矩;往往不可其意,则归臣于家,叹息忧愧辄不食。”接着他拿出英国人来做对比。他说,英国人素能固守习惯,对习俗移人的道理认识透彻。他们治理上海租界华人聚居区的污秽,不求速效。“英国人能顾全居民之习惯,因势而利导之,其步骤虽缓,其成绩甚大。”[1]也就是说,英国人知道,移风易俗必须行之以渐。
(一)
英国人重习惯,这是举世皆知的。英国是宪政的摇篮,但是居然拿不出一部让人读了一目了然的宪法。所谓的“the English Constitution”在历史进程中有机形成,无数杂乱无章的文书和习惯构成其主要内容,很多做法和规矩都是不成文的。英语中的“不成文”(unwritten)一词有“依照惯例和习俗为人所接受、承袭”之意,因而不成文法往往有保守因循的特点,有时会被冠之以“传统”之名。英国史学界多左翼人士,他们会考查“传统”如何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被制造出来,而“习惯”(custom)一说可能被用来维护不公正的现状(见霍布斯鲍姆编于1983年的《发明传统》一书)。虽然习惯在英国的政治文化中非常重要,雷蒙·威廉斯却没有在《关键词》一书中收入关于“习惯”的辞条,此举背后有明显的政治动机。威廉斯在“传统”的辞条末尾补充道,“传统主义”是一个贬义词,“似乎用来专指妨碍任何改革的习惯或信念”。可见“习惯”一词有维护特权之嫌。其实不尽然,不成文的习惯也可能是普通民众寻求某种社会保护的依据。
就政治谱系而言,杰出的英国史学家爱·帕·汤普森与威廉斯同出一源,两人同为英国“新左派”的元老。与威廉斯不同的是,汤普森更注重历史细节,更愿意发掘习惯在具体的社会进程中的积极作用。汤普森对民间习惯产生学术兴趣,也许是因为他深深怀疑“文化”这种笼统提法是否能真正推进历史研究。他的这本《共有的习惯》向读者展示了“习惯”在18世纪英国社会中的丰富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