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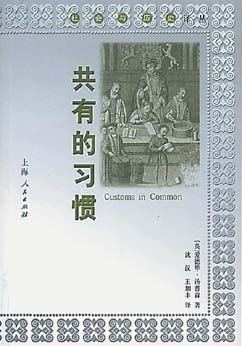 刚做历史系本科生时,我很喜欢钱穆先生的《中国史学名著》和《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因为自己当时读书理解能力有限,这两本类似讲演授课的著作,想来应是比较容易亲近钱先生精深学术的利济津梁。 刚做历史系本科生时,我很喜欢钱穆先生的《中国史学名著》和《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因为自己当时读书理解能力有限,这两本类似讲演授课的著作,想来应是比较容易亲近钱先生精深学术的利济津梁。
对刚接触现代史学的新生而言,我觉得余英时的《历史与思想》很有助益,该书展现一位秀异史家如何精彩结合传统史料与当代欧美史学、社会科学概念的分析综合功力。大三左右,林毓生带回经他消化诠释的哈耶克、迈克尔·博兰尼,在台湾掀起些风潮。我由林先生的《思想与人物》获益不少,对他介绍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如何严格要求研究生细索各种“原典”的教育理念,以及林先生以此经验为基础而提倡的“比慢精神”,很是神往;我至今仍依稀记得,当时夹生夹熟地咀嚼柏拉图《克里同》的乐趣。
大四毕业前夕,原欲改读农业经济学的志愿因故未能贯彻,我终于报考了历史研究所。当时我抱定决心,就算未录取,至少也要在离别历史系前好好读本中国通史。大概是考前两个月吧,除了准备西洋通史等应考科目外,我把力气主要花在《国史大纲》上,这项决定使我对中国史自身变迁大势有进一步理解,至今仍觉受益无穷。
进入台湾大学历史所第一个学期,修习古伟瀛老师的“西方中国史学名著选读”,与古老师合译了美国史家柯保安(内地译为柯文)甫出版的新作:《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回顾与前瞻》(内地译为《在中国发现历史》)。研读此书至少对我有两个好处:一是其标举的“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取径”,正好堪与《国史大纲》所论中国历史变迁精义相比较;二是这书介绍的种种中国社会停滞论,正好成为我读书思考时的主要论敌,这些论敌隐约激发我以《国史大纲》所习精义与其辩驳的动力,并勾起我修课与写论文的热情。
当时台大历史所的明清史师资阵容很强大,除了我的指导老师徐泓先生外,刘翠溶、郑培凯、刘石吉、梁其姿、石锦等先生都陆续开课,使我对明清史的兴趣愈来愈广。除了明清史外,中国上古、中古史的重要海内外学者,也常是当时系主任徐泓教授邀约开课的对象,我十分庆幸,赶上了当年台大历史所办学的盛况。
无论是老师们介绍的明清史重要研究,或是读《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愈知晓这些作品的基本理路,便愈让我感到《国史大纲》传递的中国历史内部变迁动力仍有许多可发挥处,这直接影响了我的硕士论文对“行会”问题的讨论。
写博士论文时,我将研究重心放在明清苏州商人团体与社会变迁间的关系,研究取径则侧重都市史“公共领域”与经济史“制度创新”等议题,这些研究取径的发展,与阅读社会科学著作有较多关连。
在社会科学之外,我自本科生起,即在校外随一位老先生读“四书五经”与几部子书,老先生讲“夏学”、宗主熊十力先生学术,懵懂之间,我在这样一种每周上课一到两个晚上的“夏学”私塾呆了好多年,直到博士班三年级某天,那是个大雨滂沱的周六午后,研究生室一片清肃,我读着熊十力先生《读经示要》,对老先生经常耳提面命的“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等“群学”要旨,以及“见群龙无首,吉”、“使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等传统政治理想,似有会心。此后,这种经验似也形成一种时隐时显的综摄力量,对自己后来的研究甚至是抉择未来志业,都有一定影响。我想,若拿《读经示要》配合《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阅读,未尝不是认识自己所属人群如何想象“理想社会”的好方法。
我主要研究经济史,以目前的有限阅读经验论,我觉得交易成本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史,以及经济人类学,都是很可推介的次学科。前者以科斯为首,他的《企业、市场与法律》所收多篇论文已是经典之作,我常拿张五常的博雅诠释对照科斯著作阅读;至于制度经济史,我很喜欢道格拉斯·诺斯说故事的方式,也努力研读其著作(目前已有三部中译:《西方世界的兴起》、《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成就》。台湾“清华大学”经济系的刘瑞华,对诺斯著作有较地道说明)。
经济人类学方面,黄应贵先生的授课大纲深具体系与脉络(可在网络上找到);而对历史系学生而言,卡尔·博兰尼的《巨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台湾出版的中译本导论很精要,既可看到这位与哈耶克针锋相对的学者如何剖析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史,也可引导读者认识“实质论”经济人类学如何看待“市场”与国家间的复杂关系);另外,选编英国史学家爱德华·汤普森重要论文的专书《共有的习惯》也极富洞识。两书都是这方面较易亲近的经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