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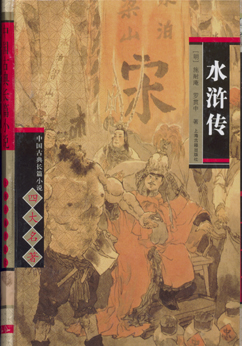 “劫富”之后 “劫富济贫”,这是梁山好汉等群体最喜欢扛出来的招牌。“劫富是为了济贫”,英雄们这样承诺,良善百姓也如是期望。然而,事实真有口号这么动人吗? “劫富”之后 “劫富济贫”,这是梁山好汉等群体最喜欢扛出来的招牌。“劫富是为了济贫”,英雄们这样承诺,良善百姓也如是期望。然而,事实真有口号这么动人吗?
我们可以试观梁山好汉做下的第一笔“买卖”。大奸臣蔡京的女婿梁中书搜刮民财,攒下十万贯金银珠宝,准备运到京城给丈人拜寿,刘唐劝诱晁盖,晁盖劝诱吴用,吴用又劝诱阮氏兄弟,那说辞均是“不义之财,取之何碍!”这话很有鼓动性,但谁有资格界定财富的“义”与“不义”?即使是“不义之财”,是否每个人都能随便取之?这些问题都略嫌复杂,且不去管它。我更感兴趣的是这不义之财生辰纲到手之后的事,书中说得明白,晁盖吴用等人在庄中饮酒作乐,“三阮得了钱财,自回石碣村去了”。看来,这笔不义之财不过是按出力大小一分了事。这也没什么奇怪的,想当初他们准备劫取生辰纲时,盘算的就是“下半辈子快活”啊。
如果说智取生辰纲那会儿的好汉们还没有多少组织性,难免自行其事不讲章法,那么已经揭竿而起并成为一支官府不可小觑的造反武装后,又如何呢?梁山群雄在宋江的率领下,颇打了一些胜仗,接连攻下了高唐州、华州、青州、祝家庄、曾头市、东平府,收益甚大,仅青州一役,斩获府库金帛、米粮,就整整“装载了五六百车”,正是这些财富――姑且算不义之财,奠定了梁山好汉们“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秤分金银”这种写意生活的基础,可是我们却几乎看不到曾有平民百姓在这一场接着一场的残酷厮杀中获益,唯独祝家庄中那位老汉,因为曾助石秀脱险,并间接使梁山大军逃脱罗网,才在宋江“不是你这个老人面上有恩,把你这个村坊尽数洗荡了,不留一家”的恐吓下,得了“一包金帛”!
“劫富是为了济贫”云云,基本上只是一个美好的神话。可是不论事实的真相如何,碾压在底层的人们仍然乐于传播这一神话,甚至常常喜欢主动把这个神话编织得更为圆满,这是什么道理呢?就因为这个神话寄寓了小生产者的理想,当他们对生活绝望的时候,就希望有一种神奇而又正大无私的力量重新分配世间的财富,这是他们的梦想和精神支柱,在很多时候,他们宁愿这个梦想缥缈些,也不愿意其在眼前活生生地破碎。所以,他们造出了许多给自己圆梦的无私英雄。另一方面,因为底层人们这种对无私英雄的渴望,“劫富济贫”又成为豪强们凝聚人心屡试不爽的旗帜。不要以为《水浒》不过是小说家言,就是在宋朝,那位史有其人的造反领袖钟相,因为说过“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这句名言,不仅在当时引来大批追随者,并很荣幸地在身后获得了当代史学家的高度评价,但史料显示,就在钟相向追随者许愿的同时,却聚敛了大量惊人的财富。
劫富之后,是不是就一定没有人出来济贫呢?也不尽然。《史记》中有关于刘邦造反后从不济贫到济贫的经过,“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原来,贪图个人享乐的刘邦突然一变为乐于周济百姓是别有深意!可是,这种隐藏极深用心的“济贫”对穷人来说,是否一定是一种福音呢?答案早已被历史的无数次轮回所验证,不说也罢。
一边惩恶,一边帮凶——“武松醉打蒋门神”别议 《水浒》里,“武松打蒋门神”是一出大戏。武松铁拳到处,一个恶势力的代表人物轰然倒下,演绎着水浒英雄“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的主题,端的大快人心。
然而武二郎在为谁鸣不平?施恩父子也。书中说得明白,施恩他爹乃孟州城监狱的管营,这位管营老爷品性如何呢?武松作为犯人最初解到时,因为没有“孝敬”,管营大人差点照常规赏给武松一顿“杀威棒”,好歹在旁边的施恩另有打算,才免却皮肉之苦。这样看来,施恩的老子其实和当时多数墨吏一样,有钱好办事,无钱就会找人晦气。至于施恩本人,他自己也交待得极为清楚,他在孟州城黄金地段开的快活林酒店并非寻常,据其对武松介绍:“但有过路妓女之人,到那里来时,先要来参见小弟,然后许他去趁食。那许多去处,每朝每日,都有闲钱,月终也有三二百两银子寻觅,如此赚钱。”这不就是今之所谓收取保护费么?施恩的本钱是什么?无非是他老子的权势,和他本人曾“学得些小枪棒在手”,书中还写道,他的酒店之所以独霸孟州,还靠他老子管的八九十个拼命囚徒护场子,这小子也真能利用一切资源呢。可是“如此赚钱”的勾当却活生生被蒋门神夺了。蒋门神又有多少本钱,为何偏偏压过施恩一头?无他,拳头更大,后台更硬,所以一场火并下来,快活林换了主人,人们转而向蒋门神上交保护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