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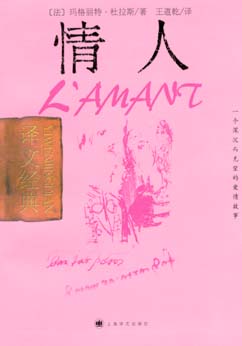 爱,是人类永恒的话题,这样说肯定没有人反驳。即使在最荒诞的年代,爱也会隐藏在土牢和乡间,成为人类忍受苦难、生生不息的巨大动力。在写作中,爱是孕育无限可能的子宫:山川河流,祖国家庭,亲朋爱人,等等等等,都可以在爱中找到合适的、惟一的表达。尤其是爱情,更是文学作品中最具魅力的血肉,千百年来,不同的爱情故事,令人或追慕向往,或唏嘘不已。 爱,是人类永恒的话题,这样说肯定没有人反驳。即使在最荒诞的年代,爱也会隐藏在土牢和乡间,成为人类忍受苦难、生生不息的巨大动力。在写作中,爱是孕育无限可能的子宫:山川河流,祖国家庭,亲朋爱人,等等等等,都可以在爱中找到合适的、惟一的表达。尤其是爱情,更是文学作品中最具魅力的血肉,千百年来,不同的爱情故事,令人或追慕向往,或唏嘘不已。
英伦才子阿兰·德波顿的《爱情笔记》,更是直接打出爱情的招牌。这部冲击了英国图书排行榜的作品,读来并不像《罗米欧与朱丽叶》、《荆棘鸟》、《简·爱》、《呼啸山庄》、《傲慢与偏见》、《情人》等经典爱情故事那样缠绵悱恻、忠贞不渝、地老天荒、刻骨铭心,它几乎没有情节,而更像是随笔。在“我”与克洛艾短暂的爱情里,作者悟到了诸如爱情恐怖主义、禁欲主义、理性、非理性的欲望等因素对爱情的影响。作者最后不无调侃地让男主人公粉碎了爱情神话,让活生生的情欲代替了关于爱情的种种玄思默想。或许,这就是作者最想告诉读者的:在泛爱的背景下,真正的爱却是迷惑的;爱情没有惟一的模式,只要你愿意,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关于爱情的笔记版本。
之所以在读完《爱情笔记》后重读美国心理学家弗罗姆的《爱的艺术》,是因为《爱情笔记》更多地把爱归到了不受理性支配的情感冲动,而弗罗姆否定的恰恰就是这种不可靠的感觉。弗罗姆不是小说家,他没有编织什么爱情故事,而是从生理、心理、社会、伦理等方面考察爱的种种表现和动机。在弗罗姆的爱的体系里,爱不是偶然的,它是可以完善的一种品格,是理性的、成熟的、宽容的人性,是一种能力。正如作者所言:“如果不努力发展自己的全部人格,任何爱的试图都会失败;如果没有爱他人的能力,自己在爱情生活中也永远不会得到满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