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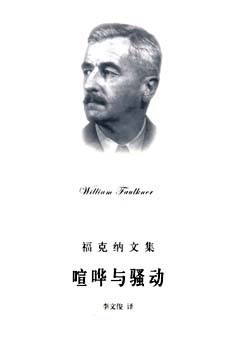 “一个人做事不在于数量多,质量要精。”今年74岁的李文俊先生回顾自己走过的路时,得出这样的体会。最让李文俊先生感到不枉此生的事,就是翻译介绍了美国重要作家福克纳。在西方现代文学中,福克纳的作品以艰深著称,而李文俊以令人钦佩的勇气和毅力啃下了这块硬骨头,翻译了福克纳最艰深的作品。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福克纳文集》7部作品中,李文俊译了4部重要作品,有《喧哗与骚动》、《押沙龙,押沙龙!》、《我弥留之际》、《去吧,摩西》。李文俊很得意地说起法国福克纳专家莫里斯库安德鲁译过多部福克纳作品,惟独未译《押沙龙,押沙龙!》,晚年,他拣起此书想译,已觉力不从心,这成为他一生中最遗憾的事。李文俊在他65岁到68岁即1995年到1998年这三年间翻译了这部福克纳最难译的作品,完成了此生最大的心愿,他因此把自己累垮了,发作了心肌梗塞。而他对此无怨无悔,他除了翻译福克纳作品,还写了福克纳评传和画传,编译了《福克纳评论集》,现在又在译《福克纳随笔全编》,觉得对得起福克纳这位大师了。做成了自己最想做的事,快乐莫大于此,即使付出代价也在所不惜。 “一个人做事不在于数量多,质量要精。”今年74岁的李文俊先生回顾自己走过的路时,得出这样的体会。最让李文俊先生感到不枉此生的事,就是翻译介绍了美国重要作家福克纳。在西方现代文学中,福克纳的作品以艰深著称,而李文俊以令人钦佩的勇气和毅力啃下了这块硬骨头,翻译了福克纳最艰深的作品。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福克纳文集》7部作品中,李文俊译了4部重要作品,有《喧哗与骚动》、《押沙龙,押沙龙!》、《我弥留之际》、《去吧,摩西》。李文俊很得意地说起法国福克纳专家莫里斯库安德鲁译过多部福克纳作品,惟独未译《押沙龙,押沙龙!》,晚年,他拣起此书想译,已觉力不从心,这成为他一生中最遗憾的事。李文俊在他65岁到68岁即1995年到1998年这三年间翻译了这部福克纳最难译的作品,完成了此生最大的心愿,他因此把自己累垮了,发作了心肌梗塞。而他对此无怨无悔,他除了翻译福克纳作品,还写了福克纳评传和画传,编译了《福克纳评论集》,现在又在译《福克纳随笔全编》,觉得对得起福克纳这位大师了。做成了自己最想做的事,快乐莫大于此,即使付出代价也在所不惜。
翻译福克纳作品的最大难题是使经常是纠结、繁缛、含混不清的原文文体,跨越两种文化的间隔,以崇尚简洁、清晰的汉语的形态出现时,仍能保持原文文本的美学价值。李文俊认为负责任的译者必须把散见各处、有的浮在表面上有的埋藏很深的“脉络”、“微血管”以至各种大小不同的“神经”一一理清,掌握好它们的来龙去脉以及所以要以这种形式出现的艺术企图,然后照它们的原样放好,并以另一种文字加以复制,而且要做得足以乱真。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李文俊开始译《喧哗与骚动》时,曾写信给钱钟书请教几个问题,钱先生在复信中说:“翻译(福克纳)恐怕吃力不讨好。你的勇气和耐心值得上帝保佑。”尽管译福克纳的一千字所费的力气可译别人的三五千字,在译《押沙龙,押沙龙!》时,每天仅能译数百字,书中长达几页的句子比比皆是,那剪不断理还乱的句子常让人掷笔兴叹,李文俊还是知难而上完成了他的翻译。之所以选中福克纳,不仅仅因为他是英美重要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最主要的原因是身为南方人的李文俊认定全世界南方人的脾气都有点相通。此外,他还喜欢福克纳的落落寡合,他的矜持,他的孤独礁石般地不理会潮流。而且,在李文俊看来,福克纳的作品有嚼头,让人回味的东西较多,比较深刻,写大家庭没落的悲哀也比表现成功者的发迹或情场得意更具美学价值。
李文俊对外国文学的喜爱从中学时代就开始了,在洋行工作的父亲和中学时学过英文的母亲从他小时候起就在外文教育上下功夫,考上复旦大学新闻系后,他选修文学和外语,并和同学一起练习翻译,出版了两部译作。毕业后他参与了《译文》(《世界文学》前身)杂志的创刊,一直干到主编然后退休。除了译介福克纳,他还参与撰写了《美国文学简史》、《大百科全书英美卷》,获过“中美文学交流奖”等奖项。
李文俊让中国读者见识了福克纳作品的精华,福克纳被介绍进来后,也在我国创作者中引起过一阵热潮。最初出现的是浅层的表面性的模仿,如生硬搬用没有标点的长句子等。但仍有一些作家能感受到这位大师真正内在、独特的艺术魅力,并将其有机地、不着痕迹地融进自己的创作中,如莫言、余华、赵玫等都谈过福克纳对自己的影响。
李文俊认为翻译工作介绍优秀的作品给人欣赏,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给文学家以滋养;在语言方面引入复杂化的语言结构,丰富我们的语言;在思维方式等方面推动文化的发展。歌德说翻译家某种意义上是民族精神上的先知。李文俊觉得这项工作很有意思。
译完《押沙龙,押沙龙!》,李文俊感到完成了一件大事。病后两年不做事觉得难受,他又拿起了译笔,翻译一些较轻松的东西,如塞林格的《九故事》、儿童小说《小公主》、《小爵爷》等,还学会了用电脑写文章,译得最过瘾的是简·奥斯丁的《爱玛》,那种细腻、俏皮、严谨的风格很对自己的脾气,这部作品触及到文学到底是什么的根本问题,即帮助我们认识自己。闲暇时,逛逛旧货市场、买菜、散步都很有乐趣。
李文俊引用了美国诗人的一首诗《行人寥落的小径》,意思是在一个分叉的路口,选择一条路走下去,不管是否还有更好的路,最后达到了目的地。李文俊选了一条自己的路,他达到了目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