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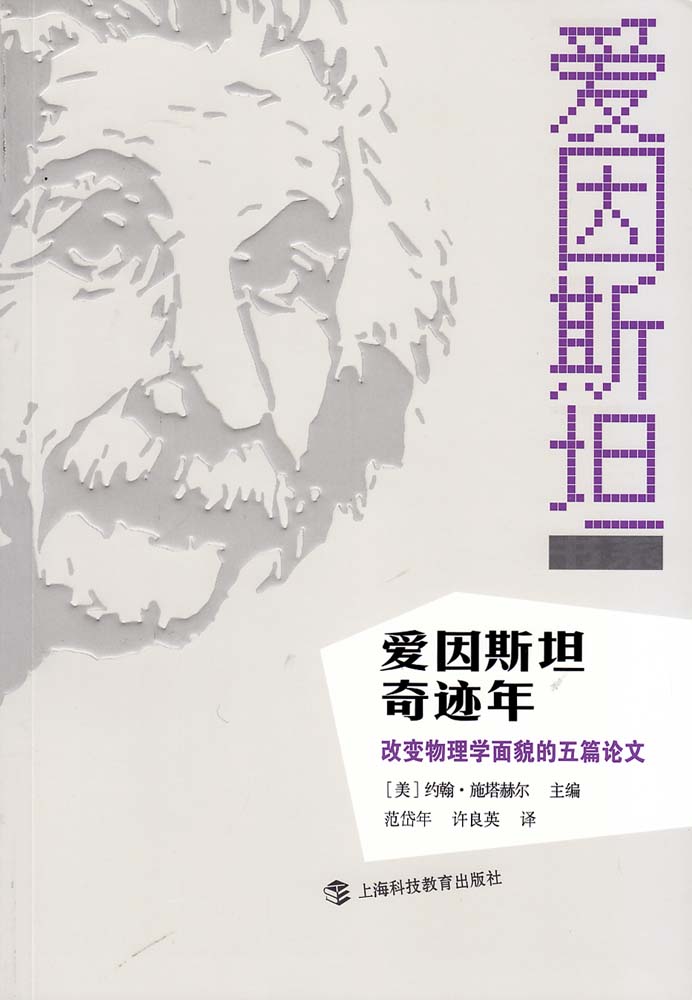 1665~1667年间,牛顿因躲避瘟疫而离开剑桥到故乡度过几年,牛顿在那几年中得出了微分学思想,创立了万有引力定律,还将可见光分解为单色光,在数学、力学、光学三个领域都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奇迹年”这个拉丁语词(annus mirabilis)原本就是用来称呼牛顿的1666年的,后来也被用来称呼爱因斯坦的1905年。 1665~1667年间,牛顿因躲避瘟疫而离开剑桥到故乡度过几年,牛顿在那几年中得出了微分学思想,创立了万有引力定律,还将可见光分解为单色光,在数学、力学、光学三个领域都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奇迹年”这个拉丁语词(annus mirabilis)原本就是用来称呼牛顿的1666年的,后来也被用来称呼爱因斯坦的1905年。
确实,1905年是“爱因斯坦奇迹年”——这一年中,26岁的爱因斯坦发表了5篇划时代的科学论文,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创立狭义相对论的《论动体的电动力学》和《物体的惯性同它所含的能量有关吗?》。一年之内,爱因斯坦在布朗运动、量子论和狭义相对论这三个方面都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这些贡献中的任何一个都足以赢得诺贝尔奖。牛顿的1666年和爱因斯坦的1905年确实是交相辉映的两个“奇迹年”。
如今“爱因斯坦奇迹年”又过去100周年了。在纪念这个不同凡响的年份的喧嚣中,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
前几天,一份报纸的编辑对我做网上访谈,也问到了这个问题。当时我是这样回答的:“应该做的事,以及可以做的事都很多吧。包括对于物理学界自身有意义的事,以及对于物理学界之外的其他学者和公众有意义的事。其中,我想对于物理学知识、物理学精神、像爱因斯坦这样的重要的物理学家事迹的传播,也应该是很重要的该做的事吧。”
当然,这样的回答有些一本正经。更实际地讲,我们甚至可以设想,人们为什么会要设置那么多的什么什么年、什么什么月,以及什么什么日之类的纪念呢?在这些纪念中,人们又都应该或者可以做些什么呢?
我注意到,在你的提问中,也即“在纪念这个不同凡响的年份的喧嚣中”这种说法里,似乎另外隐藏着一些潜台词。“不同凡响的年份”,以及“暄嚣”这两个概念,一个提示着我们去作历史回顾,以回答为什么这个年份不同凡,而另一个似乎暗示着对现状的看法。我想,历史与当下的比较,或许是我们纪念“奇迹年”时可以做的重要事情之一吧。
那就先回顾一把吧。我感到,了解在1905之前那几年爱因斯坦的生活和工作状况,对我们今天的科学发展,乃至对所谓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都有教益。
爱因斯坦1900年毕业于苏黎世综合技术学院,该校被认为是当时欧洲最好的学校之一。爱因斯坦进这所学校也不顺利,第一次投考不幸名落孙山,他不得不进入瑞士的一所补习学校(那时就有“高考复习班”了呢),1897年他才如愿以偿。在大学里,爱因斯坦很快就和女同学米列娃堕入情网。米列娃生于奥匈帝国的官宦之家,从小就有才女的声望,爱因斯坦和她珠胎暗结,她不得不回到父母家生下了孩子(一个女儿,可能不久就夭折了),这使她未能通过毕业考试,当然也就无法得到文凭——这是一个典型的女大学生“早恋”并婚前怀孕而导致学业失败的悲惨故事。
名校毕业文凭并未能让爱因斯坦求职顺利,他到处打零工,晃荡了两年功夫,直到1902年6月,经一位同学的父亲推荐,才在伯尔尼专利局获得一份三级技术鉴定员的工作,年薪3500法郎。任务是鉴定新发明的各种仪器,其中主要是机电产品。1903年他和米列娃结了婚。因米列娃没有文凭,无法找到工作,次年长子汉斯又出生了,相当沉重的家庭负担,使得这位专利局的年轻职员那几年的生活看起来颇有点潦倒落魄。
一个专利局的小职员,当然没有机会与当时的主流科学家来往。爱因斯坦在伯尔尼只有几个青年朋友,最重要的是哈比希特(Habicht)和索洛文(Solovine),还有哈比希特的一个小弟弟。这一小群年轻人经常在工余和课后聚首,一起散步,或在寓所一起阅读、座谈。他们研读的哲学和科学著作有:斯宾诺莎、休谟的著作,马赫、阿芬那留斯、毕尔生的著作,安培的《科学的哲学经验》,物理学家亥姆霍兹的文章,数学家黎曼的著名演讲《论作为几何学基础的假设》,戴德金、克利福德的数学论文,彭加勒的《科学和假设》,等等。他们也不“重理轻文”——他们还一起读过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拉辛的作品、狄更斯的《圣诞故事》、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以及世界文学中许多别的代表作品。
一起阅读的乐趣在于思想的交流,这群年轻人被这种乐趣迷住了,虽然清贫,但是他们充实而幸福,感到“欢乐的贫困是最美好的事”。他们将这难忘的几年命名为“不朽的奥林匹亚学院”。
是的,100年前,爱因斯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和环境下,创造出了属于他的“奇迹年”。“奇迹年”中的科学成就,在此后的100年间,再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一年中(甚至在许多年中)做出如此集中而且如此革命性的成就。不过,我们却看到,爱因斯坦的研究,是完全以他个人对于科学的兴趣而做出的,并无如今这样形形色色的科研基金资助,也不属于什么科研规划的一部分。当然,他的工作,也不是以为了获得什么什么等级的奖励为目的,尽管由于他的工作他后来还是获得了诺贝尔奖,而且只是以他在这一年中的一项工作获得的。人们现在通常认为,他那年的其他几项工作,也可以当之无愧地获得诺贝奖,只是由于当时的某些争议,诺贝尔奖评选者的认识甚?要完备得更迟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