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有不一样的出发点。
我深信如果一个人对于某些思想充满了信念,那这个人就有职责去传播这些思想,哪怕这过程意味着自我破坏。我经常对于那些对我感兴趣的事物无感的人充满好奇,经常会去想:怎么才能抓住这个人的注意力呢?怎么才能去诱惑他们,让他们对原本毫无兴趣的领域产生好奇心呢?
《外滩画报》:
这种执念是怎么来的?
阿兰·德波顿:
有可能是这样的:小时候我喜欢并且看了很多书,我对书的作者充满了崇敬。另一方面,我崇敬的家长却对这些作者和书毫无兴趣。这刺痛了我。我的很多家人和朋友都很聪明,但他们对“智慧”不求甚解。这种“知识分子”与“普通人”之间的鸿沟很没有必要。我自问:那么好的书应该是给所有人看的。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我们都会孤独,都会焦虑,都在受苦,最后都会死去。这些问题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每个人都需要在生活里去面对。可我觉得,在西方社会的今天,对于个体灵魂来说很重要的“新闻”并不足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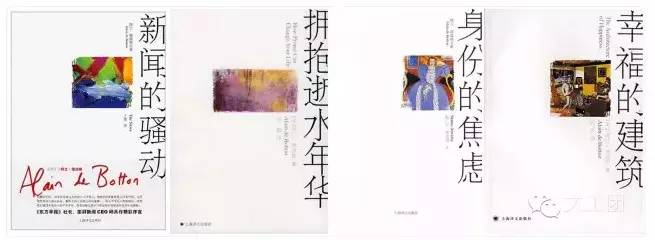
德波顿算得上是多产的作家,而他的作品几乎全都有中译本,由此可见他在中国受欢迎的程度。他在去年出版的《新闻的骚动》中探索大众媒体处理新闻的方式
未来将是个体度身定做的新闻时代
《外滩画报》:
这是你写作去年出版的书《新闻的骚动》的动机吗?
阿兰·德波顿:
很有意思的是,对于很多人来说,每天读报,看天下发生什么大事很重要。很多人觉得要是不随时看新闻的更新,就不能算是很严肃地对待生活。我不这么看。大众媒体对于我们生活中“什么是重要的事”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它们建构了我们的思维模式。这些天,估计在伦敦看新闻的所有人都在想着叙利亚难民的事情。可是大众媒体处理新闻的方式从来是断章取义而且有局限性,这是个问题。
看看今天我们往前走的方向吧,我想,任何自称从事文化工作的人,都不可能再回避人与人的沟通。我们不可能回到过去精英阶级主导的旧社会,我们生活在大众文化的时代。
《外滩画报》:
可还是会有人自视为“精英”?
阿兰·德波顿:
当然会有,但“精英们”对今日社会不再有影响力。你看,牛津大学哲学系教授、剑桥大学文学系教授是谁?没有人知道。可是人人都知道默多克在《太阳报》上都说了什么。我们容许一个社会朝着这样的方向发展:人人去聆听未必很聪明、很有趣的声音,这是消费与民主社会派生的问题。去思考知识分子在这种社会中有着怎么样的身份,是个挑战。
《外滩画报》:
去年你开了一个“Philosophers' Mail”的新闻网页。
阿兰·德波顿:
那是一个实验,现在网页已经关掉了。当时我们想用讽刺手法去仿效英国一张八卦小报、也是最受欢迎的网络新闻端《每日邮报》(The Daily Mail)。这张报纸每天都在八明星轶事,我们就用哲学的角度去解读斯泰勒·威夫特的大长腿、布拉德·皮特的假日,我们想颠覆大家的思维:没有什么八卦是不可以严肃认真去解读的。这么做是想去改变我们司空见惯的小报腔调。
《外滩画报》:
你认为,什么是真正必要的新闻?
阿兰·德波顿:
这并没有统一答案,得看每一个个体自身需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现在也许还不成气候,但一两个世纪以后将是个体度身定做的新闻(personalised news)时代。最重要的新闻将是每一个人此时此刻最需要了解的新闻,以帮助自我成长为人格更完善的版本。有些人也许需要更多地了解移民形势,有些人也许需要更多地了解“谅解”,不一而足。
今天大众媒体的问题就在于规定了所有人必须关注那几件事。而不少有心理问题的人都在利用大众媒体去分散对自我的注意力,以逃避现实,而生活在由新闻事件堆积成的虚拟世界里。这个世界里没有个人生活的方向、不需要责任心、不需要处理感情关系和人际互动,只有抽象的事物。
《外滩画报》:
我们现在可以做些什么呢?
阿兰·德波顿:
带着更多的自我意识去消费新闻,这种个人化的读报习惯,有时候还意味着刻意不去读报。
《外滩画报》:
你是要说,信息爆炸时代会消减个体独立思考的习惯?
阿兰·德波顿:
肯定会的,信息爆炸频繁分散注意力,也暴露了人性中一些很糟糕的方面,比如说以牙还牙的报复心、毫无耐性地对他人做出草率的评判、愤怒等,这些经常见于社交媒体中。有时候看推特上满屏的戾气,觉得整件事就像一场严重的精神病。
《外滩画报》:
因此社交媒体会影响到情商?
阿兰·德波顿:
这确实会成为情商发展的一块绊脚石。
《外滩画报》:
但同时你也在Youtube上开了个频道:School of Life(生活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