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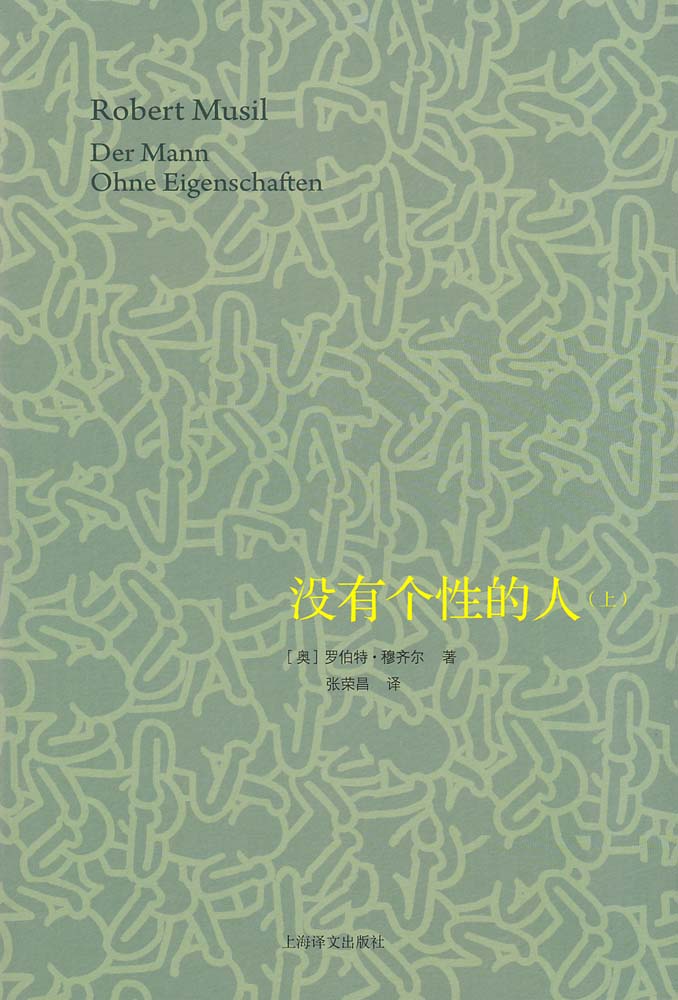 在奥地利作家罗伯特·穆齐尔眼中,传统小说中的几大要素——人物、情节、布局等并不是最重要的,相较于“精神”,它们可能只能沦为陪衬。但这并不意味着穆齐尔重直觉、轻理性,恰恰相反,穆齐尔是一个喜欢将感性和潜意识的东西通过理性手法表现出来的作家,这让他的作品有了一股亦庄亦谐的气质。 在奥地利作家罗伯特·穆齐尔眼中,传统小说中的几大要素——人物、情节、布局等并不是最重要的,相较于“精神”,它们可能只能沦为陪衬。但这并不意味着穆齐尔重直觉、轻理性,恰恰相反,穆齐尔是一个喜欢将感性和潜意识的东西通过理性手法表现出来的作家,这让他的作品有了一股亦庄亦谐的气质。
文学上的“巴托比症候群”,是指那些因各种原因拖稿、赖稿,以致最终没能交稿的作家。此症候群作家主要分两类,一种是江郎才尽型,如晚年的杜鲁门·卡波特,一种是精雕细刻型,如罗伯特·穆齐尔。44岁那年,穆齐尔说服出版社给他支付生活费用,让他全身心地投入一本小说的创作。此后近20年,只有当出版社上门催稿,穆齐尔才会像挤牙膏似的透一点篇章出来。直至1942年去世,小说也没有写完,但它已然是一部包含12000页、10万个注释的鸿篇巨制。今天,这本名叫《没有个性的人》的小说被誉为“20世纪最重要的文学成就之一”。
其实,这也是一本我们花上一辈子的时间,也未必能读完、读透的小说。因为,这是一本完全迥异于传统小说,甚至迥异于“小说”这种体裁的作品。没错,它有一个故事的框架—1913年,德奥两国为各自的君主筹备登基纪念大典,主人公乌尔里希应召加入这一“平行行动”,参与、见识了上流社会的种种面貌—但也仅仅只是框架而已。威廉二世,以及茜茜公主的老丈夫弗兰茨·约瑟夫一世,连同“平行行动”一道,到头来都只是跑了跑龙套,打了打酱油罢了。故事,在穆齐尔眼中,是完全不作数的。
那么,穆齐尔写作的焦点是什么呢?我们不妨用小说中的一个情节来加以说明。小说开篇时,乌尔里希站在自家寓所的窗户后面,观察各种街景,“一直对着表在数小卧车、汽车、电车和行人那被距离冲洗得模糊不清的面孔……他估算着从一旁移动过去的群体的速度、角度、活力,它们像闪电一样快地把视线吸引、抓住、松开……”
乌尔里希在看,但是,他也在被人看,被谁看呢?被穆齐尔。穆齐尔就像一个运动神经专家,细细测量着乌尔里希在追踪别的东西时,眼部肌肉的功能、注意力的跳跃、心灵的摆动。他跟他笔下的主人公一样,“像玩耍似的试图计算出这不可能计算出来的东西——一个数值”。
这个例子,说明了小说的两种写法。一类是传统小说,着眼于细细描摹外物世界,包括它的政治、经济、人文,以及“世态人心”这样一些东西。比如,我们要了解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社会变迁,那么,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就是很好的选择。另一类,就是像《没有个性的人》这样的纯“精神”小说。这个“精神”,不仅是相对于“物质”而言,更重要的是,它还是对传统小说中的几大要素—人物、情节、布局等—的“逆袭”。这些东西,在穆齐尔的小说中,并非不重要,但绝非很重要。他让它们统统后退为背景,登到前台来的,是传统小说中通常作为陪侍人物、情节、布局的“丫鬟”——精神。
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个性的人》与乔伊斯、普鲁斯特和伍尔夫等人开创的意识流或内心独白手法,一脉相承。因为后者的意识流或内心独白,往往强调意识的不规则,重直觉、轻理性。而穆齐尔,恰恰是一个重理性,甚至将一些感性、直觉、潜意识的东西通过理性手法表现出来的作家。说来并不奇怪,穆齐尔在柏林大学主修哲学和心理学,辅修数学和物理学。可以说,文理兼备使《没有个性的人》别具一种纵横捭阖,要深度有深度、要视野有视野的气质。
有趣的是,这种气质,也让小说读起来透出一股既严肃又谐谑的味道。“三观”不正是常态,但它的不正,是用很正经的话语,亦可以说是学霸式的语言讲出来的。比如,两情缱绻,总有腻烦、嫌恶的时候吧?但穆齐尔不说腻烦和嫌恶,而是用一些诸如“干瘪”这样的生理词汇、“专制”这样的政治词汇、“僵直”、“限制”这样的哲学词汇,哄得被甩的情人一愣一愣的,也顺便帮读者将“腻烦”这类抽象的概念做了足以引起上述联想的移情和解说。
而穆齐尔对一些更“高大上”意义上的话题,如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宗教神学,也如法炮制,做了这类看似让人觉得不无道理,但细想之下又觉得岂有此理的阐说。这类故作正经的胡扯,有时看起来像是赞美,有时看起来像是讽刺,而有时候,我们简直弄不清作者的倾向。但无论如何,穆齐尔教会我们对那些板上钉钉、确凿无误的事物,作出应有的质疑,而非毫无保留的认同。
米兰·昆德拉在文论集《被背叛的遗嘱》中,将穆齐尔与卡夫卡、布洛赫、贡布罗维奇等人并列为欧洲头等作家,“他们将随笔式的思考引入到小说艺术中;他们使小说构造变得更自由;为离题的神聊重新赢得权利;为小说注入非严肃的与游戏的精神……尤其是他们不想硬塞给读者一个真实的幻觉”。我想,《没有个性的人》的最大贡献,可能就在于穆齐尔通过各种手段,将附丽于“现代现实的秘密运行体制”上的种种“幻象”,剥除得一干二净。尽管这些秘密本身,未必被他全部揭示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