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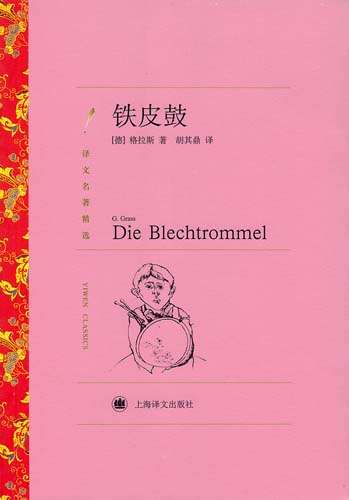 德国名导演施隆多夫这阵子访华,谈得最多、也是被问得最多的题目之一,就是1979年根据君特·格拉斯同名小说改编的《铁皮鼓》。在我的印象中,《铁皮鼓》是极其少有的质量不逊于原著的名著改编片,饰奥斯卡·马策拉特的演员贝内特,之后再也没有演过什么让人记得住的片子——他似乎就是为一个片子而生的。 德国名导演施隆多夫这阵子访华,谈得最多、也是被问得最多的题目之一,就是1979年根据君特·格拉斯同名小说改编的《铁皮鼓》。在我的印象中,《铁皮鼓》是极其少有的质量不逊于原著的名著改编片,饰奥斯卡·马策拉特的演员贝内特,之后再也没有演过什么让人记得住的片子——他似乎就是为一个片子而生的。
但读过书的人还是知道,施隆多夫只拍了原著不到三分之一的内容,到奥斯卡的父亲被枪杀,他的外祖母,那个片头套着四条裙子、在野地里搅烤土豆的女人重新出现为止。一条道路伸向远方,第三帝国覆灭,战争结束,没有下文了;观众永远记住了奥斯卡这个古怪的早熟孩子,记得他的诸多堪称邪恶的恶作剧。
奥斯卡到底象征着什么?论者说法不一,最常见的是说他象征纳粹德国的罪恶,甚至就是影射希特勒的;他假扮耶稣,他在民众集会上敲鼓就能操纵众人,表明了这一点;有说他不止代表德国人,其象征范围扩大到了腐化堕落的人类社会;还有说他身上有被边缘化艺术家的影子:他加入侏儒剧团,用喊碎玻璃这种特异功能做无聊的表演来哗众。拥有这些互异的解读,格拉斯这部小说之成功和杰出都是毫无疑问的,每一种解读都表明了奥斯卡的一重特征,他与其他人物、与社会环境的某种互动。
《铁皮鼓》当然是对特殊年代德国社会的讽刺,它采用了一个有着大人心智的孩子的眼光来看那个社会。但看电影者一般不会将大人的一面和孩子的一面联系起来,大人的坏、狡猾、世故,和孩子的幼稚天真似乎是无关的,只是偶然地集于主人公一身。但读完书后,你就会发现,格拉斯有意安排了许多类似“成人-孩子”的对比,双重性,是把握《铁皮鼓》之魅力的一根红线。
奥斯卡有两本最喜欢的书,或许也是他唯二的书:一本就是歌德的《亲和力》,另一本则是沙俄著名的神棍拉斯普廷的回忆录,前者是日神阿波罗的唯美之书,后者是酒神狄奥尼索斯的狂欢之书,书中,过去和现在在一个句子里来回出现,人称在“我”和“他,奥斯卡”之间频繁转换,之间只隔了一个逗号;奥斯卡既是象征当下的恶童,又是一个预言未来的暗黑先知;他有两个父亲,一个是老马策拉特,头脑顽固的德国公民和天才的厨子,天才到可以只用汤来表达感情,另一个是花花公子、成天活在白日梦里的布隆斯基,他在波兰邮局被德军攻陷后枪杀——这两人一个代表德国,一个代表波兰,一个是西方,一个是东方,一个是行动,另一个是念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