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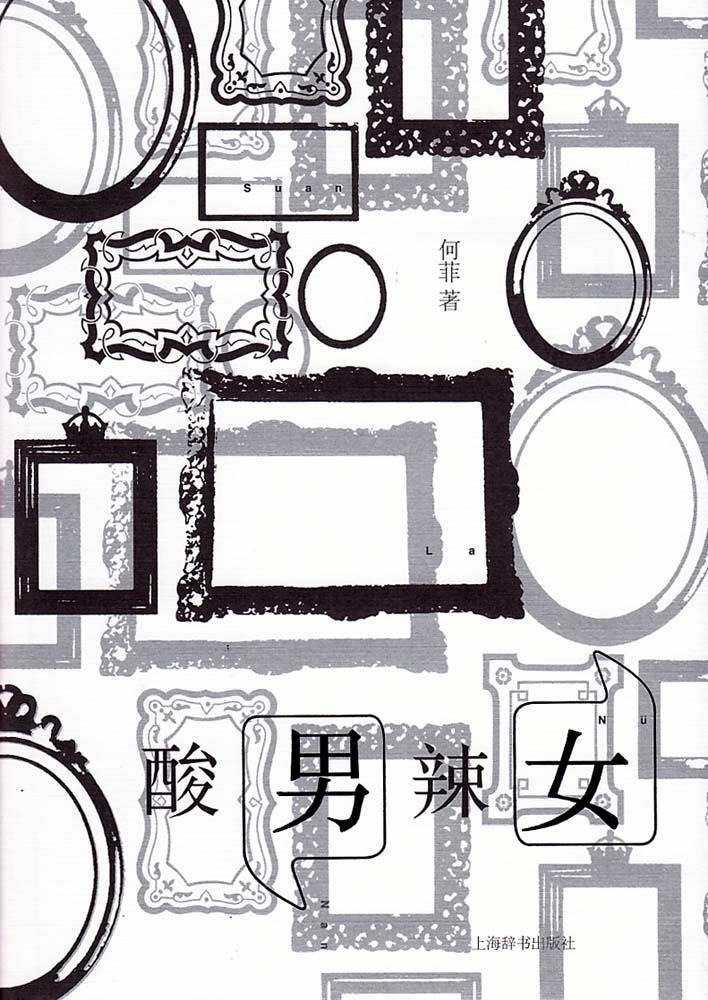 S是我青春时代的密友,我们初见面便一拍即合。我们在草地上喝利乐砖冰红茶,吃全赤豆棒冰,冒着35℃高温去吃兰州拉面,在那间足以洗桑拿的简陋空间里大汗淋漓地吃着三块钱的拉面,高声谈笑,然后去宿舍楼道里那间只有冷水供应的浴室冲凉。身上久久飘着舒肤佳香皂的香味。那是上海20世纪90年代中期大学校园里独有的夏天气息,如此年轻与落拓。 S是我青春时代的密友,我们初见面便一拍即合。我们在草地上喝利乐砖冰红茶,吃全赤豆棒冰,冒着35℃高温去吃兰州拉面,在那间足以洗桑拿的简陋空间里大汗淋漓地吃着三块钱的拉面,高声谈笑,然后去宿舍楼道里那间只有冷水供应的浴室冲凉。身上久久飘着舒肤佳香皂的香味。那是上海20世纪90年代中期大学校园里独有的夏天气息,如此年轻与落拓。
那是一段尽情挥霍青春和爱情的岁月。那时候的爱情,无非是一阵抽象的激动过后,搅得内心翻腾回旋的浅水而已。在阵阵余波中,原本干燥的天气没来由地飘起毛毛细雨,聆听已然错乱的心跳,身怀某种倦意在无限的心海里做深呼吸,混杂着青草和广玉兰被揉碎的情绪。那是怎样澎湃的荷尔蒙啊,能让所有现实的困惑和心灵的际遇经历一次次膨胀缩小的轮回,最终在无边的彤云中逍遥逍遥。
S在我的毕业纪念册上写:上帝给了你精致的底子,也给了你过于能体会的心,这曾经且继续会让你的幸福和痛苦变得绝对与极端。而要是让你抛弃华丽的思维去做个心思简单的女人,我想你情愿迎接随时而来的希望和随时而来的绝望。
毕业后我们见面的频率慢慢减少直至消失,约会最多的地方仍是拉面馆——日式的。缅怀青春是青春盛年时的开场白,每次回忆都让人唏嘘,后来便只谈当下。五年前,S约我去“樱”,请我吃北海道味噌拉面。她问我味道如何,我仔细品味那寒温带食物特有的粗犷的顺滑,给出评价。
S幽幽叹了口气,说她喜欢这款拉面基于和她常年中午来此消磨的男人。
可她只是他的午餐恋人,吃完这顿等下一顿,没有长期打算。这样没有预期的关系一天天随惯性运转,没有停歇的迹象,却比预想中热烈缠绵。一起吃拉面成为他们之间唯一沾地气的幸福仪式。每当两碗热腾腾的面端上,他们就会被无以名状的踏实热度包围,可同时某种幻灭感也乘机升腾而上,在享受与对抗中,不可言说的拉面情愫将他们紧紧捆绑。
走出面馆,S屡屡重新审视一道难题:除了吃拉面和极速欢愉外,他们之间还拥有什么?
直到有一天,北海道味噌拉面师傅告老还乡,新来的厨师只做冷荞麦面,吃冷面时,S得出比面条本身更平凡的答案:某些事,只是青春的大胆假设。
从那天起,S的青春结束了,也在我的生活中消失。
赵薇的“致青春”我没去看,买了张碟至今未拆封,我想S也不会去看。凭吊青春是后青春文艺人最青涩的话题。所有的挫折和失落,所有的不堪与神经病发作,只要贴上青春这块膏药,就都有了释然的理由。当不再赖在青春的原地不肯挪步,才能将失去活成一种获得。
两年多前,假期刚开始时,横在我面前的是一座大山。我夜夜噩梦:医生手持西瓜刀在我腹部比划,我挣扎,试图逃脱,手脚却被几位强壮的护士牢牢按住……对未知的恐惧在离手术前十天不可避免地爆发。
从病房到手术室的走廊很魔幻,看着很长,走着很短。阳光照进来,光柱里透着尘埃。深呼吸一口,很快我将脱胎换骨。
插上导尿管,打了麻药和镇定剂,神志却依然清醒。划开肚皮时,我的内心也开始起风。闭上眼睛,默念心经,那一刻,想起有一年在亚东我因为高原缺氧难以入眠,只听到隔壁转山藏民背着的婴儿不止的啼哭声……
叮叮当当的器械声把我拉回现实。有人用软硬交织的劲道按压我的肚子。腹部感觉在被一点点向外牵拉,然后掏搅着什么,一阵一阵,犹如巨浪拍打礁石。一直陪伴我手术全程的先生在我耳畔说,坚强些,想想我们的初相遇。
听到医生说,脚出来了。又加大力气按压,牵拉,掏搅,反反复复。又听到说,身体出来了。再反复……如此,不知晨昏。
医生说,头出来了。
听到她问先生:剪了?先生抬头看一眼挂钟:剪吧。随即听到米兔的啼哭。
吸尘声在我腹腔里久久鸣响,还有手在内里掏,扭曲的脏器带着复杂的钝痛。我忍不住叫了两声。医生说,稍微忍着点,在吸羊水,要吸干净才恢复得快。
麻醉师将小东西交到先生手里。这无法和其他任何重量相比的2 985克,被—双坚实的手臂紧紧抱住。从下望上去,只见他通体粉红,身上缀满光的粒子,顷刻照亮整个空间。先生端抱着把他凑到我眼前,这个才离开母体5分钟的家伙正在对崭新的世界左顾右盼,眼睛黑而灵活,长眼裂,深深的双眼皮。
缝针的过程尤其漫长,酸酸胀胀的,只听到医生说,再忍忍,快缝好了。然后,似乎在耻骨部位给我贴了一条胶带。
时间给人的感觉在各种情况下是不同的。4小时的手术,像跨越了一个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