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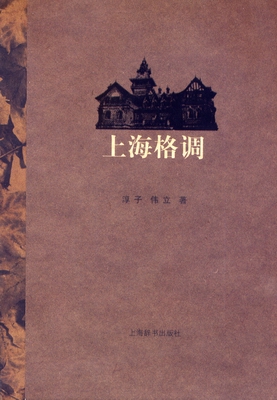 《上海格调》是那种热爱生活,赞美城市,迷恋上海,一唱三叹的咏叹调,调门蛮高的。近几年,上海街头的流行语是“腔调”,常看见一位艺人说:“做人要有腔调”。放到书里,作者们抿嘴说:“格调”,不是“腔调"。我们这一代人对上海文化的肯定,有时候会有一些夸张。我们今天遇见的纽约客、伦敦人、巴黎人,固然也都会暗赞自己城市的繁华、丰富和优雅,都市客的夸耀,在所难免,但会比较含蓄。强劲的“现代化”过去以后,骄傲的城市人会比较平静,不再那么傲视“落后”和“乡村”,乃至于向往田园,回归自然。现代人更重视对于自己生存状态的批判意识,于是反省和反讽,也就比夸耀和夸张更有力量。但是,作为一个同城同代同思考的人,我对《上海格调》中的高调的夸耀,仍然很能理解。原因很简单,我们还没有完成“现代化”,我们还在呼唤“现代性”。 (文:李天纲) 《上海格调》是那种热爱生活,赞美城市,迷恋上海,一唱三叹的咏叹调,调门蛮高的。近几年,上海街头的流行语是“腔调”,常看见一位艺人说:“做人要有腔调”。放到书里,作者们抿嘴说:“格调”,不是“腔调"。我们这一代人对上海文化的肯定,有时候会有一些夸张。我们今天遇见的纽约客、伦敦人、巴黎人,固然也都会暗赞自己城市的繁华、丰富和优雅,都市客的夸耀,在所难免,但会比较含蓄。强劲的“现代化”过去以后,骄傲的城市人会比较平静,不再那么傲视“落后”和“乡村”,乃至于向往田园,回归自然。现代人更重视对于自己生存状态的批判意识,于是反省和反讽,也就比夸耀和夸张更有力量。但是,作为一个同城同代同思考的人,我对《上海格调》中的高调的夸耀,仍然很能理解。原因很简单,我们还没有完成“现代化”,我们还在呼唤“现代性”。 (文:李天纲)
小南门警钟楼,上海的埃菲尔铁塔
离着乔家路还有两个街区,在重重叠叠的屋顶森林里,小南门警钟楼雄鸡一般,高昂着骄傲的脖子,穿越而出,霸道,不可一世。
明末清初,老城厢多为木结构民居。一点火星,便是一片火灾。1909年6月29日,上海救火联合会在信成银行召开特别议事会。
鉴于上海人口稠密,屋舍毗连,议决建筑钟楼。由朱志尧负责,求新厂制造。
朱志尧是求新造船厂的创办人,也是上海著名的慈善家。20世纪初期的上海,除江南制造局外,民营轮船制造业中规模最大的要数朱志尧的求新厂。
朱志尧家族在绍兴路、金神父路上有大片的地产。
朱家主人住在绍兴路5号,一幢华美的大洋房,西班牙古堡样式,黑色镂花铁门,车子可以直接开到大厅的台阶边。花园很大,打网球,骑自行车,游刃有余。家里的小姐生日,请来同学,在草坪上开派对,留声机里是爵士和法国女歌星。家族历史类似宋庆龄的父亲,在教会里任职,亦经营商业。
在这栋楼里,有过地下抗日组织的秘密电台,孵育了中国第一支爵士乐队,也有过无数名人名媛的轶事。
朱家人信奉慈悲,每每出门,都在衣袋里放一些铜币,撒给街上的乞丐。
此番建造警钟楼,保佑百姓生灵,只当是慈善,不计较钱两。
1910年6月18日,举行钟楼落成典礼。
钟楼高35.2米,钢材制造,重达4300多斤,结构采用中国传统玉雕的镂刻法,一层套着一层,一环牵着一环,雄伟壮观,也精巧玲珑。塔中央有螺旋梯,铸铁镂花,坚固精美。此楼是当时上海最高点。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上海革命领导人陈其美等决定起义响应。11月3日,以小南门救火联合会钟楼钟声为信号,上海商团各部、敢死队等聚集南市,宣布上海起义。
夏天里,周围的小孩子,偷偷跑进钟楼的院子里捉蟋蟀,他们最大的梦想,就是登楼望远。
人雁南飞,风沙迷眼处,一个世纪悄然逝去。钟楼的每一级阶梯上,如同碑林墨迹,爬满了历史。城门没有了,城墙没有了,那塔,便成了老城厢最醒目的坐标,是上海字典里的埃菲尔铁塔。
爱因斯坦惊鸿一瞥
站在塔上,乔家路上的梓园尽收眼底。
高高的门楣,任风吹雨打,世事变迁,“梓园”二字深深地镌刻在石头的筋骨上,如同伏笔,晕开了结局。
是午后,弄堂口,闲坐几位老人,孵在日光里,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时事,说着邻里,说着柴米油盐。
进得院子,但见一架推土机,如巨型的、战败的变形金刚,锈蚀的铁爪,无力地垂在地上。绕过横七竖八撇弃在那里的工具,兜兜转转,在二楼回廊的转角处,见到了传说中的戏台子,倚在院子的墙边,七零八落,伤痕累累,一副林黛玉受了委屈的样子。梅兰芳的水袖,周信芳的皂靴,哗啦啦的叫好、洒在戏台子上的赏钱,了然无声、无痕。
一扇门前挂晾着衣服。
敲门问路,只道是外地新聘的工人,全然不知院子的历史。
1922年11月13日,爱因斯坦访问上海。
梓园主人、海上闻人王一亭封帖子,盛邀爱因斯坦和夫人来园子一游。
自然是留饭。一顿辉煌丰盛的晚宴。
花梨木云母石圆桌,银餐具水晶杯,八大碟八小碟前菜,八热炒四大件主菜,甜咸甜心16件,两道汤品间演绎着菊花蒸蟹温酒赋诗的文人传统。
窗外的戏台上,丝竹声声,如幽兰睡莲。无关风月,全是风月。
这样的阵势,连尼德兰人也叹息不如。
爱因斯坦对上海惊鸿一瞥。日后回忆道:“在那没完没了的宴席上,尽是连欧洲人也难以想象的悖德的美味佳肴。”
爱因斯坦的夫人爱尔莎惊呼:“光是这些粮食就足够我吃上一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