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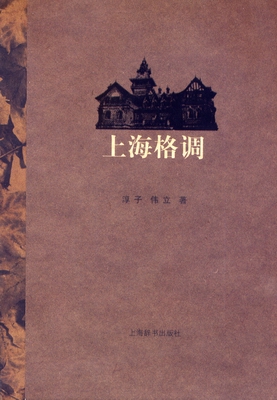 在上海,做人不能没腔调,但更要有格调。什么才是“上海格调”?新书《上海格调》(淳子、伟立著,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文笔优美,气格优雅,以衣、食、住、行、玩为主要线索,讲述真正有格调的上海人如何对待自己、他人,如何生活,怎样看待生命,兼顾上海的历史与当下。 在上海,做人不能没腔调,但更要有格调。什么才是“上海格调”?新书《上海格调》(淳子、伟立著,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文笔优美,气格优雅,以衣、食、住、行、玩为主要线索,讲述真正有格调的上海人如何对待自己、他人,如何生活,怎样看待生命,兼顾上海的历史与当下。
盛家女子超然物外
初春,坐在卢湾区图书馆的小楼里。
院子里的玉兰树,灰青的枝头上,几朵粉白,似花非花的样子,衬托出《青玉案》中“试问闲愁”的濡湿。馆长亲自搬来一摞子的民国旧报纸。
顺手,掸去上面的尘埃。总是嫌灯光黯淡,因为字迹太小。喝着馆长泡的雨前龙井,抱着可有可无的心绪,把老黄的旧纸一页页翻检过去。
一个骨感的女子入得画来。那种苏州人的瘦。那种丁香般淡淡的愁。她叫盛佩玉,是清朝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的孙女。她的母亲亦是苏州美女,嫁给盛宣怀的长子盛昌颐做妾,住在外面的小公馆。父亲去世得早,母亲只好做了曹禺戏剧《雷雨》中的鲁妈,留下了孩子,另嫁作他人妇了。盛佩玉的丈夫是盛宣怀的外孙,盛家四小姐的儿子,著名出版家邵洵美。婚礼在卡尔登饭店举行,震旦大学校长马相伯是他们的证婚人。
抗战期间,为了躲避战火,人们纷纷逃亡租界。
当时,邵洵美的红粉知己、美国作家项美丽(Emily Hahn)拿到了特别通行证,驾车去杨树浦帮助盛佩玉搬家。炸弹不时地落下来,空气中弥散着硫磺的味道。盛佩玉镇定地从玻璃橱里拿出了一套咖啡具,装进了逃难的箱子里。她心想:“打仗,咖啡总归还是要喝的。”
日子越来越难,盛佩玉不愿意求人,只有靠典当暂度。一天,盛佩玉收到典当行的通知,典当的钻石已经到期了。佩玉没有钱把东西赎回来,又不愿意去借钱。借钱是失身份的。佩玉道:“就让那些宝贝给当铺吃进了。没有首饰,也无损我的颜色的!”
解放以后,盛佩玉做了居委会里的小组长。他们在淮海路的房子先是借给居委会开食堂,后来又借给居委会办托儿所。一大家子人,就剩了一间屋子。
邵洵美身体不好,她就把这间房子留给了丈夫,自己去江苏路的女婿家落脚。
那个时代,每个人的命运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盛佩玉来到女婿家,惊讶地看见了张爱玲的继母孙用番租住在一个十平方米的小屋里。孙用番的父亲是做过民国政府总理的孙宝琦,与盛宣怀家是亲家。弄堂里的小孩子都叫孙用番“姑姑”,她是一位高雅的老太太,面容端庄,极有风度,老了,依旧还是白皙,到底是享过福的人,身段还摆在那里的,脑子亦是清楚得不得了。标标准准的京片子,很有一些舞台的味道。孙用番会注射,弄堂里有小孩子生病,就请她过去打针。她孤身一人,却把日子过得稳稳当当。和邻居合用一个保姆,冲冲热水瓶,磨磨芝麻粉。她喜欢弄堂里乖的小孩,把他们叫来,给他们吃蜜饯、糖果、芝麻糊。她一直是靠变卖家产来维持晚年生活的。早先,她的房间虽逼仄,家具都是值钱的老货,座钟、相架都精致美观,连盛芝麻糊的碗盏、调羹都是古董。她半盲以后,五官在脸上都走位了,手里的拐杖依然还是德国的老货色。
她的身体无可奈何地衰弱下去,家具也越卖越少。但是当她出现在弄堂里的时候,依旧是一个干干净净、腰板笔直的老太太,哪里肯随便地将息。这是体面,也是尊严。盛佩玉自然知道张爱玲与继母间的纠结。她道:“孙用番一直照料着张爱玲的父亲,替他送终,这已经足够了。”语气里满是悲悯。
盛佩玉在南京居住时,买了几个鸭肫干寄给邵洵美。
洵美回信说,不舍得吃,挂在那里,用舌尖浅尝辄止。
盛佩玉得了癌症,医生说,少抽烟吧。
一晚,是冬至,盛佩玉托出烟缸道:“此刻,我吸今生最后一支烟。”就此戒了,没有一点点的牵丝攀藤。
这一代豪门闺秀,大富大贵,大起大落,有辛酸,却没有抱怨,处变不惊,随遇而安,超然物外,修成圆觉。
出得小楼,已是黄昏,正下着雨,小径旁的竹子,有潇湘馆里的雨声。馆长在身后道:“就一起吃晚饭吧,咸肉菜饭黄豆汤,还有评弹。”
于是折回去,任往事在上海人的食谱里,在零落的吴侬琵琶里,欲语还休。
“闲话”里的那点骨气
我一直觉得上海话是很虚心的,无论想讲什么意思,都自谦为“闲话”。在上海方言里是没有单音节的“话”字的,只要是嘴巴里讲出来的都是“闲话”,即使是郑重其事的要言警句。
上海的吴阿姨对邻居、北方人李太太讲:“我规规矩矩脱侬讲几句要紧闲话。”李太太听起来,闲话多少有些多余、无聊的意思,能有啥要紧的呢?吴阿姨强调的“规规矩矩”到底还是落空的。
但是,上海人大多还是守着上海话自命清高,他们彼此之间是不屑讲普通话的,谁开口讲普通话,通常都会被揶揄为“开国语”。意思里,像是一个平头百姓硬着头皮讲“官话”,狗嘴里吐“象牙”,自以为起了身价。
大约是由于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缘故,上海人对京城官话的官僚傲气很敏感,感到官话实在不如上海闲话的乡音更近人间烟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