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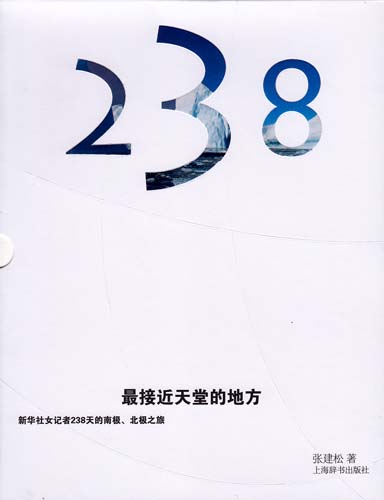 从小,视野所及的天际线尽头,只有层峦叠嶂的大别山。我的故乡在安徽省岳西县,那里是大别山革命老区。 从小,视野所及的天际线尽头,只有层峦叠嶂的大别山。我的故乡在安徽省岳西县,那里是大别山革命老区。
大别山像母亲温暖的怀抱,抚育了我的成长;大别山又像一道森严屏障,将我与外面的世界阻隔。山外是怎样的一番世界?连绵起伏的大山像一个个扯不直的问号,让我充满好奇,追索答案。这,也是我努力学习的不倦动力。
如今,感谢“新华社记者”这份职业,让我几乎每天都可以看见外面的世界,甚至有机会到地球的南北两极去看一看。
为了圆这个梦,我在新华社做了整整十年的准备
记得十多年前,我刚进新华社上海分社,第一次到中国极地研究中心采访,神秘、孤独、绝美、纯洁的南极引起了我心中的无限好奇。从此,去看一看那里的世界,成为我心中一个遥远的梦。
为了圆这个梦,我在新华社做了整整十年的准备。
终于,当自身和外界的各项条件均已成熟时,2007年11月,我作为新华社历史上第一位赴南极采访的女记者,跟随中国第24次南极科学考察队出发了。
这次考察历时156天,我们乘坐“雪龙”号横跨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南大洋,四次穿越西风带“鬼门关”,往返于以凶险著称的德雷克海峡,多次遭遇西风带强气旋的“围追堵截”,航程28450海里,相当于环绕地球航行一周。
这是一段充满激情的人生历程,是我十年记者生涯中最快乐、最单纯、最过瘾的一段时光。
去过南极之后,如果还有机会去北极,也许任何人都不会放弃。我也是这样。
2010年7月,我跟随中国第四次北极科学考察队前往北极采访报道。这次考察历时82天,我们乘坐“雪龙”号在茫茫大海航行近13000海里,南北纵贯2300海里,东西横跨1100海里。从白令海、楚科奇海、加拿大海盆,到门捷列夫海脊、弗莱彻深海平原,最后抵达北极点附近海域。“雪龙”号最北抵达北纬88度26分,创造了中国北极考察史和航海史上的多项新纪录。
在这次考察过程中,我还有幸和部分考察队员乘坐直升机抵达北极点,成为新华社历史上第一位抵达北极点采访的女记者。
北极之行值得骄傲的还有,由于这次考察正值2010年上海世博会举办之际,经过新华社上海分社慎海雄社长的周密策划,在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和全体考察队员的大力支持下,在“雪龙”号进入北极圈那一刻,我组织了“问候祖国 祝福世博”活动,为世博会的成功举办遥送一份来自北极的祝福,并将世博会会旗成功地插上了北极点。
这是在人类历史上,世博会旗帜第一次插在了地球的最北端。为了留下永远的纪念,新华社上海分社还专门制作了“世博北极点纪念章”,为世博文化增添了一份别样的光彩。
为什么要去南极?这个质疑曾令我深思许久,也令我内疚许久
去南极之前,我在新华网上开了一个博客,许多网友纷纷留言为我祝福,但也有少数网友提出质疑:为什么要去南极?
“如果很多人都怀有你这样的热情,南极就惨了!地球几乎没有处女地给你们玩了,多为地球想想吧!戈尔《难以忽视的真相》,难道你不看吗?!”一位匿名网友在留言中这样质疑。
为什么要去南极?这个质疑曾令我深思许久,也令我内疚许久。
因为我是报道极地的媒体工作者,公众至今还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到南极去,说明我们的宣传报道工作还做得远远不够。
按照人们单纯、善良的理解,如果人类的脚步永远不去涉足南极这块净土,就是对南极环境最大的保护。
但事实是,在过去的200多年里,人类对南极的涉足从未停止过。南极洲作为当今世界上唯一没有公认主权的大陆,自从被人类发现以来,国际社会关于南极的纷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从1772年英国探险家库克率领两艘独桅船到南极寻找“未知大陆”的环球航行,到1819年俄罗斯军官别林斯高晋和拉扎列夫率领南极探险队奔赴南极;从1895年开始的南极探险英雄时代,到1911年阿蒙森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到达南极点、斯科特捐躯南极冰原,一批又一批探险家前赴后继地涉足南极。如今,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南极早已经不再是几个探险家小心翼翼触摸的神秘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