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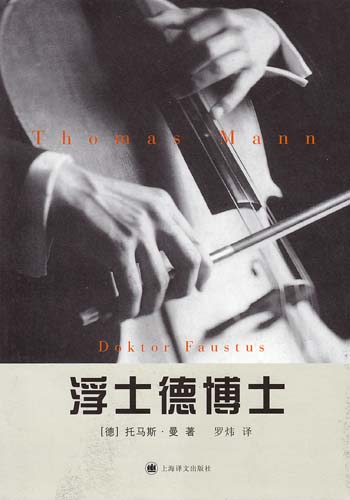 托马斯·曼在中国也很有名,这不仅因他早在1929年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还因为早在半个世纪以前的1962年,他的成名之作《布登勃洛克一家》的中译本也在中国出版了。小说甫一问世,好评如潮,洛阳纸贵,托氏这《一家》便飞进了万户千家。这个家族四代人的命运引起中国人的关注。从此,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托氏的作品一部接着一部地译成了中文。1947年就已发表的、托氏本人视为“最爱”的《浮士德博士》,有多少人对其抱有期望,但迟迟不见出场,直至前几个月才由译文出版社出版。它之所以“千呼万唤始出来”,此无他,乃是因为它的艰深,德文译者很少有人“偏向虎山行”。它涉及中世纪的历史和文化,涉及神学、哲学、基督教、自然科学、音乐,乃至作曲技巧。着手翻译,译者便处于形形色色专有名词和术语的轰炸之中;书中那种阴森的气氛也很难用中文描摹;托氏直接引证欧洲各国语言的引文,译者所面对的不止是德语,还有古高地德语、法语、英语、意大利语、拉丁语、希腊语。将这些引言译成中文是颇费周章的。罗炜女士用十年之功将其译成中文,相信“十年辛苦不寻常”。 托马斯·曼在中国也很有名,这不仅因他早在1929年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还因为早在半个世纪以前的1962年,他的成名之作《布登勃洛克一家》的中译本也在中国出版了。小说甫一问世,好评如潮,洛阳纸贵,托氏这《一家》便飞进了万户千家。这个家族四代人的命运引起中国人的关注。从此,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托氏的作品一部接着一部地译成了中文。1947年就已发表的、托氏本人视为“最爱”的《浮士德博士》,有多少人对其抱有期望,但迟迟不见出场,直至前几个月才由译文出版社出版。它之所以“千呼万唤始出来”,此无他,乃是因为它的艰深,德文译者很少有人“偏向虎山行”。它涉及中世纪的历史和文化,涉及神学、哲学、基督教、自然科学、音乐,乃至作曲技巧。着手翻译,译者便处于形形色色专有名词和术语的轰炸之中;书中那种阴森的气氛也很难用中文描摹;托氏直接引证欧洲各国语言的引文,译者所面对的不止是德语,还有古高地德语、法语、英语、意大利语、拉丁语、希腊语。将这些引言译成中文是颇费周章的。罗炜女士用十年之功将其译成中文,相信“十年辛苦不寻常”。
托马斯·曼一直思索探究德国人的气质、心性、根性,或者说德国人的精气神。在他看来,德国人是二律背反的矛盾统一体:一方面胸怀世界,另一方面又惧怕世界;一方面有着世界主义的大气,另一方面又显示出狭隘地方主义的小家子气。托马斯曾悲叹:“德国人的与世隔绝,德国人的不谙世事,德国人与世交往的笨拙,而这一切都采取了现代民族主义的形式。在过去的年代,民族主义与一种市侩的普遍主义和褊狭的世界主义一起体现出德国人的精神面貌。”这样的精神面貌有一种乖戾之气,好似幽灵在游荡。托氏的家乡是吕贝克,本是一个“明智、清醒的现代商业城市”,居民信仰新教者居多。可那千回百转的街巷,细节繁复的哥特式尖顶教堂,绘满死亡之舞图画的圣母教堂,这一切使人嗅到“潜伏着精神瘟疫的气息”。可以说,托马斯·曼对德国的灾难早就有所感知,有所预见。早在上个世纪初他就计划写一部关于浮士德博士的梅毒艺术家的故事。
浮士德的故事是德国作家竞相采用的题材,最早来自十六世纪出现的民间故事《约翰·浮士德博士的故事》。浮士德实有其人,和马丁·路德是同时代人。他是占星学家、数学家和郎中,浪迹江湖,占卜行医,玩魔术,变戏法,并与当时的许多学者名人相过从,还经常吟诵荷马的史诗。他的特异之处还在于不信上帝,渴求知识,不懈追求。传说他为了探索宇宙和人类的奥秘,竟然与魔鬼结盟,并签下二十四年的契约,将灵魂出卖给魔鬼。在魔鬼的帮助之下,他上天入地,召来亚历山大大帝,唤来绝代美女海伦,并与之生了一个孩子。临终之时,他对其不信上帝、离经叛道、与魔鬼为伍、出卖灵魂的一生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和忏悔,要他的学生不要学样,要以他为戒。出版这一民间故事的法兰克福出版商约翰·施皮斯不是为浮士德树碑立传,而是将其作为“反面教材”来警示世人。然而十六世纪是文艺复兴时期,科学不再是“教会恭顺的婢女”,对宇宙的探索必然会逾越宗教信仰的界限,“供批判用”的“反面教材”,往往被那些“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的巨人或精英分子正面吸收,反其意而用之,于是浮士德反而成了他们笔下的英雄。英国著名戏剧家克里斯朵夫·马洛、德国民族文学奠基人莱辛、歌德、海涅等也都以浮士德为题材写过剧本或小说。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则另辟蹊径。如果说歌德的《浮士德》呈现的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上下求索最终得以救赎的巨人形象,托氏的《浮士德博士》则呈现了资产阶级没落时期精神文化的病态和败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