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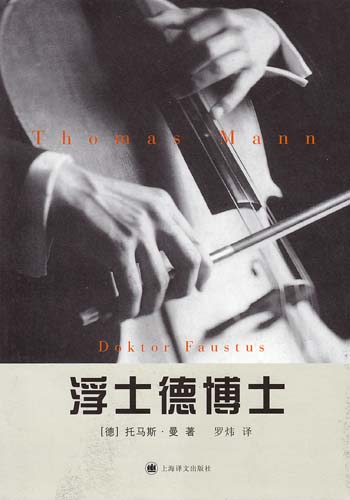 描摹世事百态,剖析人物命运,在思考人性善恶中探索,多半是小说家故事的灵魂寄寓。德国著名作家托马斯·曼在他的《浮士德博士》中,驱使民间传说的神秘色彩,人鬼交往的阴森氛围,从头到脚渲染,甚至可以说浸泡故事的整个躯体。 描摹世事百态,剖析人物命运,在思考人性善恶中探索,多半是小说家故事的灵魂寄寓。德国著名作家托马斯·曼在他的《浮士德博士》中,驱使民间传说的神秘色彩,人鬼交往的阴森氛围,从头到脚渲染,甚至可以说浸泡故事的整个躯体。
《浮士德博士》描写音乐家阿德里安为了取得个人事业的成功,不惜先是感染梅毒,继而与魔鬼结盟,由此获得魔鬼许诺的超越其自身局限的艺术灵感,创作出一部又一部惊世骇俗之作如《约翰启示录》、《浮士德博士哀歌》等等。阿德里安支付的代价是,他24年不可以有爱的生活,以及24年后他的灵魂归魔鬼所有。在这个情节脉络上,衍生出的是阿德里安与他的家世,他与亲属、朋友、老师的交往,以及他的情爱纠葛。按照常理,这样的故事情节,很容易让读者听任悬念的诱惑,俯首贴耳地沉浸在作者的文字里,一如游客在一名巧舌如簧的导游指引下,便捷地游历着名胜古迹。况且神秘色彩、阴森氛围,又如同分量合适的添加剂,时不时绘影绘声地现身于小说的某个场景中。例如:为阿德里安治疗梅毒的两位医师都有着莫名其妙的不祥结局:一人死亡,一人被捕;阿德里安与魔鬼签约时,魔鬼的一次次变形和阿德里安感觉到的凛冽刺骨的寒意;阿德里安凭借恶魔赋予的灵感创作的《约翰启示录》在演奏时,音符居然如同混杂着嘶吼、尖叫、鬼哭狼嚎般来自地狱那充满嘲讽的胜利狂笑……尽管有它们凑趣地挑逗着阅读的快感,但阅读小说《浮士德博士》却与阅读一般的神话传奇截然不同。
在《浮士德博士》中,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马斯·曼以小说主人公、音乐家阿德里安的个人人生传记来解读探究德国的命运——德意志民族受诅咒的原委。于是哲学思辨的浓重、音乐术语的聚集、宗教神学的知识,以及两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历史,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纳粹帝国穷途末路的写照,频繁出没于小说的字里行间。概念的词汇、思索的感悟、史料的追述与形象的描绘,并驾齐驱,此起彼伏。倘若说神秘色彩、阴森氛围是《浮士德博士》文本对读者的挑逗,它们则是《浮士德博士》文本对读者的挑战。所以,小说不少章节的开头都有因为篇幅的冗长而使读者有可能失去耐心的忧虑和表示歉意的文字。纵然有神秘色彩和阴森氛围,掺兑、稀释哲理的思辨,人们在作者叙述路径上的行走,仍然无法轻松。
托马斯·曼写《浮士德博士》的苦心孤诣,是刻画出卖灵魂给恶魔的德国——“是的,我们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反对理性和普遍的、具有强烈的悲剧性心灵的民族,我们的爱属于命运,任何一种命运,如果只有一种的话,哪怕它就是用众神的晚霞点燃上苍的毁灭!”作者借小说中音乐家阿德里安人生故事的讲述者之口,抒发的这番感慨,正是托马斯·曼的文学对历史的反思。
为了展示“用众神的晚霞点燃上苍的毁灭”之“德国性格”的悲剧,《浮士德博士》里的音乐家阿德里安,必须具有足够强劲容量的文化“内存”——托马斯·曼将尼采、贝多芬、舒曼等多位文化伟人的生平片断、细节糅合,融入自己塑造的阿德里安的人生遭际。唯有如此,阿德里安的个人人生传记,方才得以承载追踪、思考德意志民族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伤害世界的历史行迹。
《浮士德博士》描摹的,是出卖灵魂给恶魔的阿德里安所陷入的“孤独”和挣扎:“我很想把他的孤独比作一个深渊,在这个深渊里,别人为他付出的情感全都无声无息、无影无踪地消失。冷漠将他包裹。”即便,“他渴望更温柔、更人性的生活氛围,他希望从中获得能够促进他的创作欲和力量的,促进他未来作品的人性的内涵的善和伟大。”
《浮士德博士》思考的,是受诅咒的德意志民族的命运:“我对这个遭受厄运的民族怀有无边深厚的同情,怀有悲痛欲绝的怜悯。”“这个民族的历史本身承载着如此恐怖之极的失败,这个民族自身已经变得疯狂迷乱,这个民族的心灵已经变得枯萎干涸。”作者声称自己是“怀着一种所谓的爱国主义的豪情,来感受我们所陷入的深渊。”
或许,有文学研究者认为托马斯·曼用“受诅咒的命运”的悲剧作色彩,涂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历史行迹,是一种失之偏颇的心理学读解。倘若翻阅上海译文出版社《浮士德博士》中译本的那篇内容丰富的“译本序”,有心的读者多半会作出自己的理解。然而,托马斯·曼思考自身民族所经历的那个坠入野蛮、黑暗深渊的时代的那份执著,不禁令人倍生敬意。可能有人会用西方文学往往有“忏悔”、“赎罪”的宗教意识进行阐释,或者归咎于德国文学哲学思辨的传统,可我们应该明白,对民族灾难的回忆和追索原委,才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抑或,这正是《浮士德博士》值得品读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