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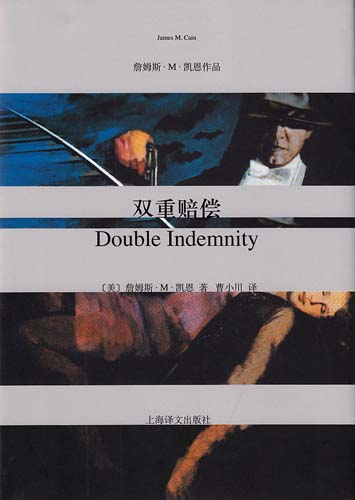 这样不可复制的阵容如今想起来简直会忧伤:《双重赔偿》(1944)。詹姆斯·M.凯恩的小说原著,雷蒙德·钱德勒的改编剧本,站在导演席上调度弗莱德·麦克莫瑞拿丝袜跟芭芭拉·史坦威克调情的是全盛时期的比利·怀尔德。还能怎样对路呢?只靠一枚打火机就能点亮一屋子影调并且盘活两个男人的前后三场内心戏的时代(请自觉在《双重赔偿》的碟片中搜索关于打火机的镜头),不是2011年的《艺术家》或者《雨果》用“技术仿古”就能真正再现的。胶片场景道具固然可以做旧,可是该怎样才能把银幕上的规定情境和观众席上对光影的敏感度,全调回黑白模式呢?事情就是这样:黑白电影的黄金时代,是看惯了彩色影像的眼睛和心灵,永远无法真正感知的。 这样不可复制的阵容如今想起来简直会忧伤:《双重赔偿》(1944)。詹姆斯·M.凯恩的小说原著,雷蒙德·钱德勒的改编剧本,站在导演席上调度弗莱德·麦克莫瑞拿丝袜跟芭芭拉·史坦威克调情的是全盛时期的比利·怀尔德。还能怎样对路呢?只靠一枚打火机就能点亮一屋子影调并且盘活两个男人的前后三场内心戏的时代(请自觉在《双重赔偿》的碟片中搜索关于打火机的镜头),不是2011年的《艺术家》或者《雨果》用“技术仿古”就能真正再现的。胶片场景道具固然可以做旧,可是该怎样才能把银幕上的规定情境和观众席上对光影的敏感度,全调回黑白模式呢?事情就是这样:黑白电影的黄金时代,是看惯了彩色影像的眼睛和心灵,永远无法真正感知的。
不过,把小说和电影放在一起看,你还是能感觉到,黑白的凯恩、黑白的钱德勒和黑白的怀尔德之间,有那么一条暧昧的灰色地带。三位大师就在一团灰色中暗战。杀人是好办的,凯恩在原著中已经吃透了保险条例和火车运行的规律,鉴于当时具备车速缓慢和尸检水平相对低下这两项客观条件,整个过程确实经得起最挑剔的推敲——钱德勒没有理由不全盘照搬。故事的前半部逻辑复杂而人性单一,正是让电影人最舒服的套路:在这个类似于“《金瓶梅》前传”的故事模型中,怀尔德只要确保在“西门庆”扼杀“武大郎”的一刹那聚焦在“潘金莲”的表情变化上,就能既忠实于原著,又不超越好莱坞的暴力尺度,顺便也让这个酷得要命的镜头成为黑色经典。
问题是,杀了人以后怎么办?电影处理得干脆利落,基本扔开小说《双重赔偿》的设定,走的反而是凯恩前一部成名作《邮差总按两遍铃》的老路:“潘金莲”和“西门庆”在得手后并没有欢天喜地如胶似漆大闹葡萄架,反而被巨大的心理压力一步步击溃了两人之间本来就脆弱的欲望纽带(“我的问题是选错了对手,”男主角这样向观众交代),无形中,互相猜疑的螺丝在一圈圈拧紧……另一方面,编剧给保险公司老板加了几场戏,悄悄改变了他在小说中始终被动的位置,那场老板深夜探访保险员的戏(女主角藏在门背后的桥段很适合发挥影像优势)以及老板与保险员虚与委蛇时进一句出一句的台词,部分满足了观众“邪不压正”的心理期待。当然,钱德勒毕竟是钱德勒,他不甘心让结局彻底滑入“邪必压正”或者“狗咬狗”的俗套,所以在男女主角拔枪相向时,没忘了陡然增加一丝诡异的温存:在说“我对你没有爱只有利用”时,女人眼含泪光,她不忍心及时补上第二枪,从而给了男人以绝地回击的机会。如是,一个你搞不清是自保还是殉情的场面出现了——我总觉得,后来的《太阳浴血记》,在处理结局时很可能受到了电影版《双重赔偿》的影响。
回过头来再看小说。那些被电影削弱的暧昧地带,那个让女主角眼含泪光的内在原因,其实在文本中历历在目——给读者造成理解障碍的,是具有巨大蒙蔽性的第一人称叙事。杀人后“我”的心理变化,那种急剧的过山车效果是“我”甚至无法向自己交代清楚的。让小说读者最困惑的情节是,为什么“我”(保险员)会在案发后突然觉得自己爱上了情妇菲丽丝的继女萝拉,并且声言是出于内疚、为了保护萝拉免受冤枉而主动向老板自首?(这条线几乎被电影完全舍弃)其实,只要稍加留意,就能发现,这既狗血又突兀的爱和“内疚”是在“我”听到萝拉单方面指控菲丽丝的“蛇蝎往事”(那意味着她对男人“只有利用没有爱”)而且认定此刻菲丽丝与萝拉的男友打得火热之后,才突然冒出来的。凯恩始终没安排这对奸夫淫妇在犯案后有机会串供,所以“打得火热”其实也完全可以理解成菲丽丝为了蒙蔽警方、间接保护“我”和她自己所做出的应激反应。然而,杀人时冷静如斯的“我”却想不到这种可能,截至此刻,他所有精密计算的本领都彻底失灵了。那么,能冲昏高度理性者头脑的是什么?恐惧,猜疑,以及,爱情。所以至少我们不能排除一种可能:他们真的有爱情,哪怕以最卑劣最令人发指最冒犯读者/观众的形式出现。
有评论认为,小说让“我”莫名其妙地“爱上”萝拉无非是为了横生枝节,最终难免沦为一处俗套的败笔。而我恰恰认为,正是这条分岔,才成了这部小说有别于小报谋杀案故事、同时也让电影改编者徒呼奈何的分野。“我”的前后矛盾、言不由衷不是作者的破绽,而是一个陷入致命诱惑的男人卖给人生的破绽。凯恩需要抵御多少叙事的诱惑,才能始终保持最为含蓄克制的笔触,不让作者视角代替人物视角,不急着替“我”自圆其说。如此步步为营之后,他知道,他安排的结局,是好莱坞编剧(哪怕是雷蒙德·钱德勒)不敢照抄的(并不是因为钱德勒刻意加入私货,而是小说中这样复杂的心理、这样费解的浪漫超过了电影语言所能表达的范畴,也会冒犯观众对于“爱情”的“正确”定义)。而对于那些有耐心反复解读其小说文本的读者而言,这个在船上戛然而止的凄冷结局,则会成为他们在恍然大悟与惘然若失间,收到的最难忘的回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