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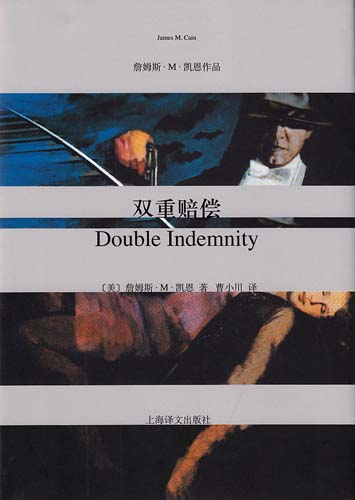 我很想知道,1944年4月的某日,刚坐进电影院的美国观众注视着片头映出的“DOUBLE INDEMNITY”(双重赔偿),边嚼爆米花边对这部派拉蒙出品的新片怀着怎样的期待。前一个晚上,他们是否从自家书架上取下那一册埃冯书局(Avon Books)版的同名小说,重温詹姆斯·凯恩那特有的语调? 我很想知道,1944年4月的某日,刚坐进电影院的美国观众注视着片头映出的“DOUBLE INDEMNITY”(双重赔偿),边嚼爆米花边对这部派拉蒙出品的新片怀着怎样的期待。前一个晚上,他们是否从自家书架上取下那一册埃冯书局(Avon Books)版的同名小说,重温詹姆斯·凯恩那特有的语调?
小说里这样的景象并未在银幕上重现:
“我起身,一手盖住他的嘴,把他的头往后拉。他两只手一把抓住了我的手……我操起一根拐杖勾在他的下巴以下……两秒钟以后他就蜷缩着瘫倒在座椅上,脖子断了……”(上海译文版《双重赔偿》,P65)头悬1934年正式生效的海斯法典,导演比利·怀尔德足够聪明,把镜头对准了正在开车的同谋者、被害人之妻菲丽丝,让她冰冷莫测的神情传达出这一残杀的最终得手。
当然,这样的句子就更与电影无缘了:
“我爱她,就像兔子爱响尾蛇。”(P106)
“只需要一滴恐惧,就能让爱冻结成恨。”(P81)
这位被埃德蒙·威尔逊称作“小报谋杀案诗人”的詹姆斯·凯恩,叙述语调极其硬朗锋利,宛如剃刀,不仅把现代人满溢的情绪当作冗余从这部第一人称叙事的作品中剔除清爽(相形之下,同名电影中的主人公画外音便略显伤感),同时也将人物对话部分“他说”、“我说”一类文本标记彻底切除。文风之劲酷,好似眼镜蛇,一下,便让人有凝血之感。
凯恩接受《巴黎评论》戴维·津瑟(Davie Zinsser)的采访时,津瑟问他有没有去看过改编的片子,他答复得口气之干脆,丝毫不比自家小说逊色:“没去看。有的吃食就有人不爱碰,我正巧不爱看电影。”另外一回访谈中,凯恩显然忘了该呼应一下,他说自己去看了这部片子,还承认“在从我小说改编的影片中,这部里头有些东西是我希望自己当初能够想到的”;提起菲丽丝去男主角的公寓,发现他同事凯斯正好在而只得躲在门后那场戏时,“真叫人手心冒汗”,凯恩说。(见加州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好莱坞黄金时代电影编剧访谈》)
真实与虚构的配比,不仅让小说家费尽思量,也永远是叫文青粉丝伤脑筋的事。
当涉及自己作品风格与语言之关系时,凯恩谈起一桩往事:当初,比利·怀尔德在好莱坞拍《双重赔偿》,总嫌合作编剧雷蒙德·钱德勒撰写的台词丢掉了原小说的精彩简洁。他甚至从派拉蒙公司的演艺班找来了学员专门训练,让他们诵读小说中的对话以资借鉴。可令怀尔德大为吃惊的是,那些对白一旦上口便全然失色,最后还是他跟钱德勒大费周章重新设计。钱德勒作为同行,事后曾专门写信给凯恩,颇为谦恭地说自己总算学到一招,凯恩书中“写”出来的对白跟他们在电影中“拍”出来的对话,各有巧妙,不是一回事啊。
“本州最高驾速不得超过每小时45英里。”
“那我开得有多快,警官?”
“我说,得有90英里。”
“假设你下了摩托车给了我张罚单。”
“假设我转而给你一次警告。”
“假设并未奏效。”
“假设我弹了你一手指。”
“假设我大哭起来把头靠在你肩膀上。”
“假设你试图把头靠在我丈夫肩膀上。”
在钱德勒和怀尔德的剧本中,男女主人公首度会面不久,就有了这段打趣,上口,顺耳,利落而令人莞尔。不过,“所有B级片的人物都聪明过头了”,Sistrom说得不错。小说里那穿了“蓝色居家睡衣”、“前额有块雀斑” 的菲丽丝,摇身一变而为银幕上半裹浴巾、光裸大腿、左脚踝上缠一圈金链的尤物;小说里,犯案之后,车厢中那个“像疯子一样咆哮,吼个不停”的菲丽丝和“我”最后“没有吻别,甚至都没有说再见”。(P78)而到了电影剧本中,“她朝他弯下身子,伸开手臂环绕住他”,“菲丽丝吻他,亲吻中他显得被动” ……黑灯瞎火的电影院里我们老这样着她的道,这迷人的、“聪明过头的”、最终把我们逼进死角的妖孽,这蛇蝎心肠美人胎,这Femme Fatale,这,才叫好莱坞。电影,跟小说自然不是一回事。
不是一回事,正如纸面上的“我”Huff并非银幕上的“他”Neff (编剧改动了名字)。怀尔德没有照搬原书中的一切,终于成就了一部佳片;而从影院中走出的人们,不少仍旧如“兔子爱响尾蛇”般扑向凯恩原作,仿佛其中蕴藏了某种不为任何改编所稀释的磁力。凯恩告诉采访人,很多人会问自己是否关心电影人对原著做的改动,他答复说,他们改动不了任何东西,他的小说还好好地搁在书架上。
小说尾章收束得清冷诡异,夜晚的大海,被鲨鱼跟随的航船,船舱里罪孽深重的男女,“月亮”悬停在最后一行,如同小说搁在凯恩的书架上。他在回复钱德勒的那封信中说,他试图在小说中攫取那种“涌流的非现实之物”。也许,他用叙述之网捕捞起的,正如月光,无处不在而又一无所在,撩拨了都市人的全部幻梦。
|